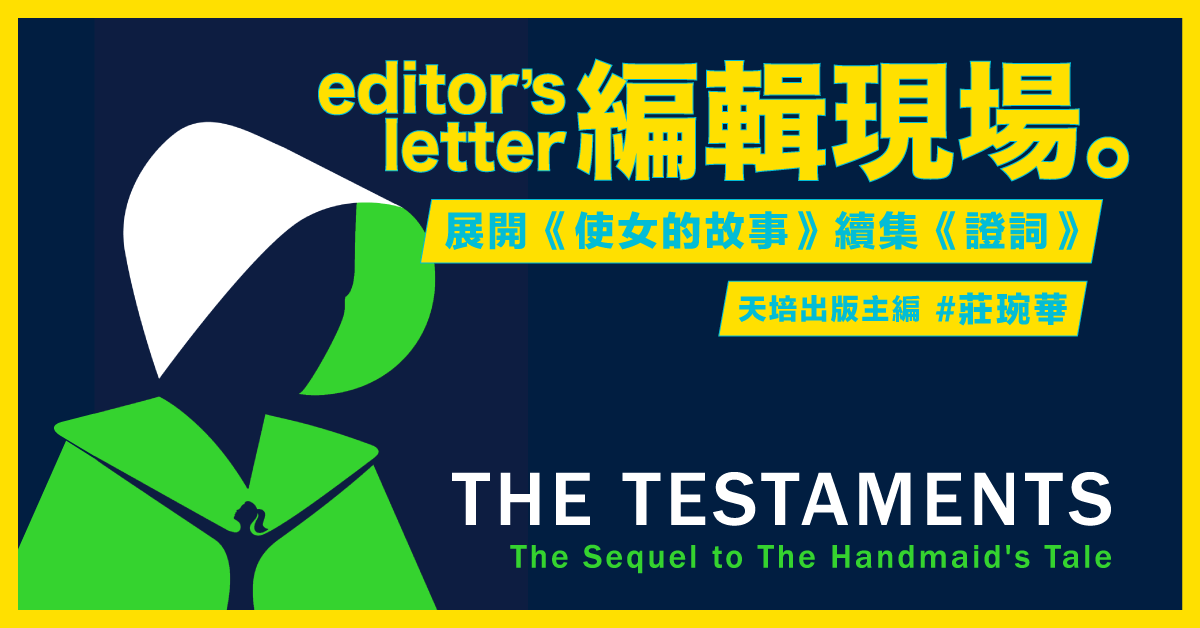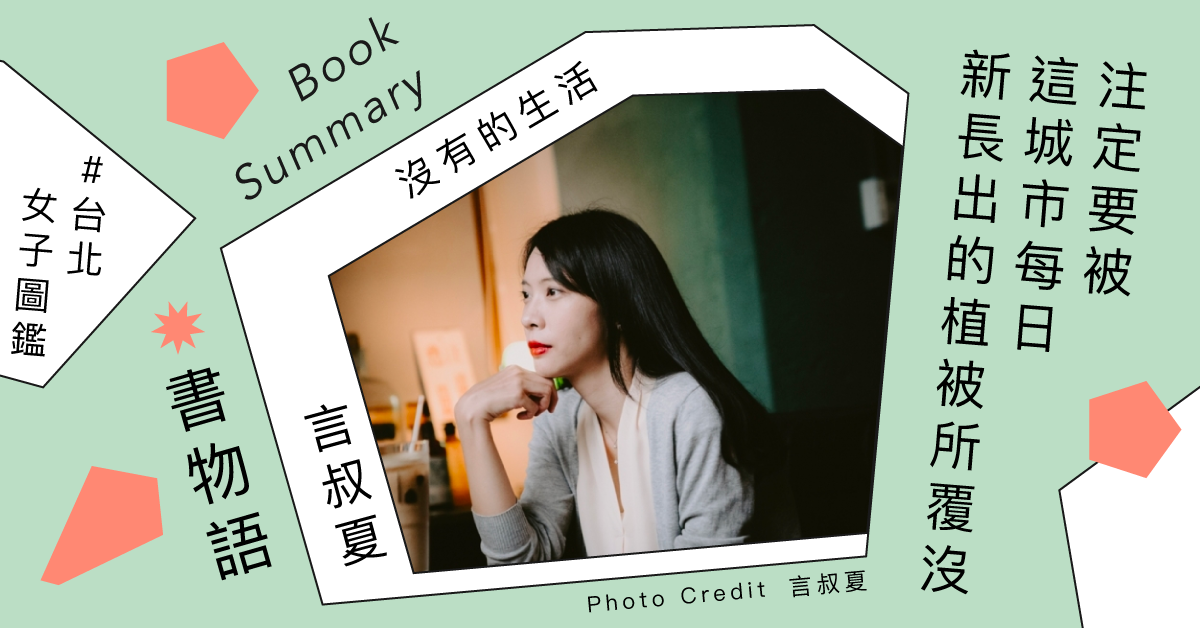直指悲傷的核心——九歌總編╳包冠涵《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
今年八月,沉潛多年的包冠涵,從生活中汲取大量素材,完成首部長篇小說《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直指悲傷的核心。
包冠涵曾寫出深受好評的短篇小說《敲昏鯨魚》(2020,九歌出版)、《B1過刊室》(2015,九歌出版),這次在新書的世界裡,透過謎樣的小女孩進行一場「探案」之旅,鋪開一場又一場死亡與重生的心靈命題。
而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以下簡稱陳)特與作者包冠涵(以下簡稱包)做了如下筆談,除讓人更深入了解《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外,也道出包冠涵的寫作時光:
陳:寫作應該是你的生活日常,你曾說過每天都會在公司附近麥當勞寫一小時再去上班?
包:我想先說說麥當勞(?),以及寫小說的時間。
可能因為我從小就是個相當散漫的傢伙(不只一次忘記把書包帶回家,也不只一次忘記揹書包到學校)因此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我想我花了相當多的心力摸索自我管理的技術,把自己教養(或馴化)成一個稍微不要那麼離譜、可以正常上下班,而且不會忘記公司的路怎麼走的大人。
那些自我管理的技術也默默感染了我寫小說的習慣。像是我在寫小說前(尤其是篇幅比較長,可能得花費比較長的時間完成的作品),我通常會建立一個excel表,excel表裡有幾個欄目,像是日期、當天預計寫字的時數、實際寫字的時數、預計完成的進度、實際完成的進度,等等的。
通常早上在麥當勞寫字的時間是一小時到三小時不等。下班之後在咖啡館寫東西的時間則通常是兩個多小時左右。寫完好我有時會到科博館附近的綠園道散散步,吹吹晚風,然後回家。如果從一個很不感性的角度來看,一篇長篇小說的完成,對我來說好像就是一個格子又一個格子裡填進去的時間。夜晚,或者白日的時間。
當然在excel的格子裡看不見許多的事物。看不見寫作遇到挫敗或挫折時那種沮喪黑暗的心情。看不見完成一個重要段落時心裡的雀躍和飽滿的幸福。看不見早晨的麥當勞裡那幾位看起來總彷彿徹夜沒睡似的臉色陰沉的人。看不見我曾經親眼目睹麥當勞叔叔的鮮黃色塑像從長凳上站起來,伸了一個大懶腰。他瞥見我在瞧他,對他眨了眨眼,踩著他的大紅鞋子來到我身邊,請求我替他保守這個秘密。
「好吧。」我說:反正我也沒什麼人可以講這種事。作為回報,我得到了一張限量的甜心卡。那張卡現在還好好地插在我的皮夾裡。
在excel的格子裡看不見許多的事物。它裡頭所有的數字幾乎只對我這個人有意義而已。我覺得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那些表格對我來說顯得如此獨特而且美麗的原因。當我慢慢地滑動電腦的浮標,看著excel中整齊的數字像無聲的鳥群或密密的雨水那樣掠過我的螢幕時,我內心總會莫名地湧起一種很踏實而且安靜的感受,好像我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究竟是如何去喜歡或者執迷於一件事的。一個格子一個格子。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清晨清晨清晨。夜晚夜晚夜晚。還有一杯一杯麥當勞的冰美式。

陳:2022年你曾在信中對我提起現在已離開了寫完《B1過刊室》時的一種自縛或隔絕的心情,完成了17萬字的長篇小說初稿,是不是就是這本26萬字的《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前身?
包:離開寫完《B1過刊室》時的一種自縛或隔絕的心情,我覺得有一個很清晰的轉折點是我在2022年寫完一篇叫〈寫東西的熊〉的短篇小說之後。我想《B1過刊室》三篇中篇小說有個共同的關切,是對文學是否有能力承受、或觸及人類痛苦這件事的質疑。寫〈寫東西的熊〉的過程好像讓我體會到,或許質疑依然存在的,也許終其一生都會存在,但書寫的自由,還有書寫或創造時的那份豐沛的快樂其實有能力包容那份質疑,與它和平共存。
在〈寫東西的熊〉那篇小說裡主角和一隻獼猴遇到了一隻寫東西的熊,他們在猜熊在寫什麼。小說裡羅列了各種書寫的可能性:
「你猜熊在寫什麼?」針對這件事,我和獼猴討論了起來。我們列舉了很多的可能性,來自我們所能想像到的各種書寫的時刻,書寫的場合。我們想,那是日記或者隨筆,裡頭寫了天氣,寫了雨水降落的時間、雲的形狀和日照在室內的挪移;我們想那是對某一樣事物的觀察,無論那樣事物在不在眼前;我們想那是記憶,以及對於記憶的警覺,對於記憶循環往復的失落和信心;我們想那是見證,是在歷歷地訴說那樣子的事情,還有那樣子的命運,是真的發生過;我們想那是食譜,寫了椰子樹苗的多汁、白蟻巢作為餐後甜點的優劣,咬碎甲蟲時口腔之內洶湧分泌的唾液,以及隨之而來的微苦。
17萬字初稿就是《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的前身。一直到我完成這份初稿並嘗試修改它之前,我都天真地以為初稿這種東西鐵定是能被修改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原來存在著無法被修改,除了捨棄重寫之外別無他法的初稿。
我把那十七萬字印出來,厚厚一本A4紙。我還幫它做了一個淺藍色的封面。
我讀第一遍,讀完後相當絕望。我把初稿放了一個月(或三個禮拜)再讀一遍。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麼。也許期待這一個月我的文學審美會產生了什麼劇變也不一定。也許一個月過去之後我會僥倖地發現它還可以。但沒有任何改變。我依然絕望。那種感覺有點像我把一根水泥柱擺了一個月,然後一個月後我再度用頭去撞水泥柱發現居然還是一樣痛。
後來我花了一些時間才克服了心理的沮喪,鼓起力氣把小說重新寫過一遍。
陳:是什麼情況下觸動你寫下這樣一部作品?
包:我有一個題庫,題目裡有五十幾個題目,有時候我會用亂數程式從這五十幾個題目中隨機抽出一個題目來做想像練習。那些題目五花八門,從「發明一種藥物」到「發明一種節日或紀念日」到「想像自己為什麼沒有來上班」都有。《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源於其中一次的想像練習,那次的練習是:想像一個你想去那邊紮營的地方。我閉上眼睛,不知道過了多久之後,在腦海中看見了亮著微弱紅光的火山口。生者、死者與動物們都圍繞著火山口,安靜地向下凝望。
我非常(幾乎是如饑似渴地)想要寫下這個畫面。可以說這個小說是從這個安靜的畫面開始的。
陳:書名有耳朵,有歌,讓人有聆聽之感。耳朵是柔軟,火山則是爆烈壯美的,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為什麼讓兩者併陳?
包:記得一開始在想書名時總是跳不開火山這個意象。畢竟火山的存在於小說背景的架設或內在意義上都佔了很大的份量。想不到好書名很焦躁,再怎麼想都跳不出火山也很煩。後來有天晚上(記得是好冷的一個晚上)我在邊譜書店跟老闆英良聊天。他告訴我他覺得書名可以朝音樂、歌或協奏曲之類的方向想,因為歌是小說裡重要的元素,書裡的角色也像協奏曲裡的樂器那樣彼此對話或合作。我覺得這實在是很棒的點子,一個新的方向。於是我開心地跑回家。
回家後又想了許多跟歌有關的書名,也還是不喜歡,直到有天「柔軟的耳朵」這幾個字的組合出現在腦子裡。我好像立刻就喜歡上這個組合,喜歡上這個意象。我覺得確實在這篇小說裡火山所指向的人們的命運,命運中的一切哀傷、痛苦或無可遁逃的種種人間情境都佔了很大的比重,但我想如果沒有一雙柔軟的耳朵,讓傾聽與傾訴成為可能的話,這篇圍繞著火山口而展開的小說其實是不會成立的。不只是角色們彼此的說話不會成立,或許這本小說也不會願意向我訴說了。我想(突然這麼想)我在敲打文字時一定也攜帶著一雙柔軟的耳朵的吧。

陳:書中有一個火山口鎮,像虛構又像寫實,有所本嗎?
包:火山口鎮是有所本的,我對它的設定很大一部分來自陽明山山仔后的美軍宿舍群。小說中,杜有恆所工作的布赫旅店原本的用途是美軍眷屬宿舍,屬於韓戰後美台軍事合作所涉及的建造工程的一環。而小說裡那一座大大的火山,則被我硬是塞進大屯火山群之中,這其實怎麼想都不現實,但我盡量地不花太多心力去思考不現實的部分(例如一座憑空長出來的火山,為什麼不會踩到原本在那邊站得好好的火山的腳,而讓它們非常生氣甚至乾脆爆發之類的),而是專注在我可以去勾勒或增加現實感的部分。
例如雖然那是一座不存在的、虛構的火山,但有師大地理系的一對學生情侶去那裡採集火山溫泉區的氣體樣本。當人們在虛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做著很實際的事的時候,我們的腦子(或至少是我的腦子)會有一瞬間覺得那好像是真的。就像如果有個朋友跟我說,他昨天去月球上的某個荒涼的小鎮住旅館,那裡的自助洗衣機壞了,他投了好幾枚銅幣進去都沒反應,我可能就會問:「靠真的假的呀?那你有跟櫃台的人講或是打給洗衣機廠商嗎?」我會(暫時地)忘了或決定不去管月球的事。
陳:周芬伶老師稱這部作品是你個人的厭世史詩,談談厭世。
包:我有時候會想人類藉由「我」這個主詞所建構起來的意識模組,是個相當中央集權的系統。或許為了生存說真的大概不得不如此。例如在大草原上,一頭豹朝我們的祖先大搖大擺地走過來,豹一手拿著胡椒鹽罐一手握著亮晶晶的餐刀,這時候存活機率最高的方法鐵定是由無數個「我」中的一個「我」大喊:「媽呀我快死了,快跑呀!」那個「我」的音量之大,會蓋過其他「我」的聲音。
例如「我-2」想著:「哇那個豹的毛看起來好好摸喔。我可以摸嗎?」「我-3」想的則是:「剛吃飽飯,好不想跑喔。跑一跑早餐吃的蛋餅吐出來怎麼辦,很浪費欸。」「我-4」則想:死一死好像也不錯,畢竟我家裡那頭長毛象的貸款都快要繳不出來了。如果這樣沒完沒了下去,人類說不定早就滅亡了。對現階段的我來說,「厭世」或許就像這樣一種「我」的中央集權的產物。它意味著有一個「我」的分貝量最大,蓋過了其他的「我」的聲音。
但即使在「我」最哀傷、最痛苦,最渴望消亡的時刻,一定有更多「我」、無數往昔的「我」、尚未誕生的「我」渴望繼續存在著的吧。我是這樣相信的。或是說:我這樣體驗過許多次。我想也是因為這樣我寫下了那個只對杜有恆受傷的身體說話的藥房老闆娘。杜有恆在火山口邊。他沒有往下跳。他說:「我知道我不會往下跳了,因為我不可能帶著身體去做這件事。我想有人溫柔地在對身體說話,那不是對我說的話,那是給身體的話,我沒有權利去打斷這件事情。」我想那位藥局老闆娘實踐了一種平等性。對待「我」的平等性。
陳:書中有跳火山的人,有「想死錯了嗎俱樂部」,主角杜有恆也是一個生活規律失婚的中年男人,這樣的設計,透露出什麼?或者說想表達什麼?
包:我覺得當杜有恆來到布赫旅店工作時,他正處在他人生中很特殊一個相對靜謐或是說過往的痛苦已經和緩了下來,而正在慢慢修復的階段。他是個失去許多重要事物的人(小說裡寫到的,至少就有:父親、母親、婚姻)而他離婚後連穩定的居所或工作型態都丟開了。當他輾轉來到布赫旅店時,他幾乎可以說是個孑然一身的傢伙。接著他在火山口附近租了個房子,開始當起了房務員。
他很用心地投入房務員這個職業所需的身體的勞動之中,像小說裡寫的那樣:『「……我習慣雙膝著地,鑽進桌子底下或是沿著牆角,用軟質的乾抹布仔仔細細把木地板抹過一遍。羅大哥從來沒有要求我跪著擦地。他一般只用靜電拖把以及吸塵器。是我自己嘗試過不同方法後決定要這樣做的,同時,我也喜歡我這樣子做過之後所顯現出來的工作成果。跪在地板上抹過每個角落與隙縫的房間,與只是站著用拖把拖過的房間,就我看來截然不同。」杜有恆想著,當花費了心神以及足夠的時間照料過一個空間之後,勞動後的雙手,的掌心,會感到彷彿積聚著一點一點的柔光的顆粒。』
我想杜有恆在旅店全心全意投入的工作像是緩慢安靜的復健,也像一個人喃喃地向著不知道什麼對象所進行的漫長禱告。就是在那樣一個剛好的時刻他遇見阿福。在那個時刻,他對於自己的生命裡的痛苦,已經稍微拉開了一點距離,這個距離讓他有餘裕去關切一個素昧平生的孩子的命運(雖然一開始他顯然沒有很情願)。同時,他自身那些悲傷的經歷,或許也讓他對他人生命中的悲哀或傷慟,產生一種想要去柔軟地包容、陪伴或撫慰的意願(雖然我相信那樣的意願,終究會帶給他痛苦)
對我來說杜有恆這個角色在小說中所位處的這個(暫時性的)空白或靜止狀態是經過思考的。我想他必須暫時保持靜止,讓他可以處在一個比較旁觀、比較外圍的位置,去(被帶動地)參與別人生命裡正在發生的一場追尋和行動。這個靜止狀態是暫時的。我想終究杜有恆會再度產生自己的動能要去完成某些際遇,畢竟他在陪著阿福追蹤「為什麼外公要跳火山?」這個謎題時自己也被改變了,像小說的第一個句子:「我曾經遇過一個偵探,一位私家偵探,她將我半哄半騙地扯進一個謎團之中,從此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

陳:全書從火山口鎮出發再回返,在一步步解鎖書中亡者最後的心靈時,「容身」二字不時出現在探索之旅中遇見的人物口中。談談容身吧。記得我們在討論書名時,你還曾想用「容身的火山」?
包:我覺得「容身」對我來說一直是一件具有真實體感的事情。可能從我小時候開始(從幼稚園?或國小低年級起)就常會在鏡子前,或是在回想自己稍早做過的事情(例如喝一瓶牛奶、睡午覺或爬到院子牆上跟一隻路過的貓咪打招呼)時,很強烈地感到:鏡子前那個人不是我。做那些事情的人也不是我。
現在我偶爾還是會有這樣的感覺的,我已經知道該如何處理或是直接忽視那種感覺。但對小時候的我來說,那樣的感覺劇烈到讓我害怕。我不知道自己是誰。從我陌生的眼睛看出去,一切都令我陌生。後來我偶然發現唸故事書可以很有效地緩和那種陌生的、驚慌的感覺。好像就是在唸著故事,在關心著故事裡角色的命運以及旅途時,我慢慢地重新聚合成一個我所熟悉的那個我。這種「被聚合」的感受,也許是為什麼我對故事始終懷有一份真的可以稱之為感激之情的原因,那也就是發生在我生命早期的關於容身的經驗。
後來上大學之後有一長段時間我都感覺到自己無法在一個地方好好待著。我翹了大多數的課,白天的時間經常就是在騎著摩托車在各個城鎮鄉鎮之間移動。好像只有在移動時,內心才會短暫地湧入一種空白或安靜。在靜止時內心反而會有許多令我難受的畫面或聲音。另一件會讓我覺得安心的事就是閱讀。那時候我常常會到書店去。在書店找到一個角落,可能是落地窗邊或書架的夾角,蜷縮在裡頭讀書。書店的空間,攤開書頁時的眼前那個鋪滿了字句的V形空間,字句所組合而成的故事或敘事,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容身。
如果沒有故事,我想很多靈魂會無處棲泊的吧。
我讀過一本叫《死亡之後》的書,作者叫Bruce Greyson,是位精神科醫師。書裡紀錄了各式各樣的瀕死經驗。其中一名叫亨利的男子的瀕死經驗特別讓我震動。亨利的父母雙亡。在母親過世後,亨利開始酗酒:他喝酒後會特別沮喪,一遍又一遍喃喃說著「家再也不是家了」。最終,憂鬱了好幾個月的他,某天喝了一整個早上的酒之後,就帶著獵槍去到埋葬父母的墓地。
作者寫道:「他在墳墓上坐了好幾個小時,時而回想,時而想像著與父母之間的對話,他決定是時候加入他們了。他躺在墳墓上,把頭放在他覺得是母親懷抱的地方。亨利將點二二口徑的狩獵步槍放在兩腿之間,將它對準下巴,然後用姆指輕輕扣了板機。」不可思議的是:「子彈撕裂了他右側的臉,在他的臉頰和太陽穴周遭留下許多碎片。但他算是運氣好,子彈沒有打到大腦。」
事後,作者詢問亨利的瀕死經驗:「……我試圖讓自己的聲音保持穩定,也避免一直看著他縫合的臉頰。」亨利描述瀕死之後所經驗的世界:我扣了板機後,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起伏的丘陵,後面的山,全都消失了……我發現自己在長滿野花的草地上。在那裡,我的爸媽張開雙臂歡迎我。我聽到媽媽對爸爸說:「亨利來了。」她聽起來很高興。但是當她看到我,表情卻變了。她搖了搖頭,說:「哦,亨利,看看你做了什麼!」
我記得讀到「哦,亨利,看看你做了什麼!」時真的是不可遏止地流下眼淚。我想人有時候並不是想死的,只是說人很難承受、很難讓自己活在一個不被愛也不被凝望的人間。這或許是為什麼在那樣的時點裡亨利的靈魂必須被他的父親與母親看見,因為我想對亨利來說,他並不是在尋死,他是本能地要去向一個可以被所愛之人凝望的所在,被凝望是他唯一可以現形的方式。對我來說這也是小說或故事這個文學形式很美好而高貴的潛力之一:去凝望,以及傾聽人類的靈魂。那同時也是容身被實踐的時刻。

陳:這算是你第一部發表的長篇小說,我知道你之前還有只是不滿意,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歷程。
包:在完成這篇長篇小說之前,可能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就一直處在很想完成一篇長篇小說的熱望中,並且我也真的實際動手去寫了好幾次。那些嘗試為我留下了從十七萬字、八萬字到三萬字不等的殘稿。卜洛克在《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裡寫過一段我覺得很迷人的話:「對於寫過長篇小說的人來說,我想寫作過程會是非常珍貴的生命體驗。它是一個非常棒的老師。而我現在所指的是它教育你認識自己的能力,而非教育你寫作之事的能力。我認為長篇小說是無可匹敵的自我探尋方式。」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的。像是我記得我曾經試著寫一篇長篇,我當時非常想實驗看看我有沒有可能寫一篇從頭到尾都在搞笑或是講垃圾話的小說。就這樣悶著頭寫了八萬多字。然後我停下來,覺得寫不下去了。我把小說印出來自己讀。一邊讀一邊覺得很想哭,不是很感人那種想哭,而是被它的難看所深深折服……我打從骨子裡意識到「光搞笑是不行的」。可能我以前隱約知道這件事,但是當花了好多個月一個字一個字去弄明白這件事,那種實際的體驗是不大一樣的。它為我留下了一種身體性的教訓,好像我真的曾經在內心跋涉時撞上了一堵牆,那堵牆其實也是我自己的血肉,我不可能如我想像的那樣自由輕巧地跨過邊界而不帶著我自己。
《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初稿完成後,我覺得它失敗了。失敗的感受並不是以一種外在的標準來看待它,覺得它不夠好或什麼的,而是內在少了一種踏實,覺得自己既沒有觸碰到什麼,也沒有在凝視中讓什麼東西現形。我陷入一段低潮期中。我沒有力氣去改它,改那十七萬字。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好像動彈不得那樣子。每當我想到那篇初稿,我的耳朵裡就會輕輕響起「算了」兩個字。
就這樣過了幾個月,很偶然地讀了保羅・奧斯特的《布魯克林的納善先生》。我記得讀完後真的彷彿從一團看不見光亮的泥淖中清醒過來。我記得書中人物傾訴自己的傷痛,那傷痛被聆聽,我也記得在說與聽之間有一種溫柔的質地是如何打動了我,我好像才終於清晰地看見自己在寫東西時心放錯了地方,在寫初稿時,我把太多心力放在如何構造一篇小說這件事上,而不是放在自己如何打開心,如何不怕受傷地寫小說這件事上。
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體悟,我發現是在我願意打開心,不怕受傷地寫小說之後,小說裡的角色似乎也才慢慢願意向我敞開他們的心。在我這個寫東西的人,與小說的角色、甚至小說的角色與角色之間,彷彿才有一種緩慢地靠近,靜靜地互相支持的關係。我想我以前似乎並未在寫東西時經驗到這樣子一種關係形式。
陳:有人說讀你的小說會聯想到村上春樹,你個人的想法是什麼?
包:我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的時候常常被逗笑。有時候是他的比喻很好笑,有時候是一些我真的不搞不懂自己為什麼會笑的點。很莫名其妙但我就是笑了。我想如果我的小說有哪些地方會讓人聯想到村上春樹的話,那一定是我被他影響了。我很難抵抗一個寫東西很好笑的作家,一定是我在一邊讀他的作品一邊咯咯笑的時候就在腦子裡吸收了他文字中的某些特質了。記得在《挪威的森林》的尾聲,村上寫玲子姐演奏披頭四的音樂:「這些人確實很了解人生的悲哀與溫柔噢。」讀那本書已經是相當多年前的事了,但我始終沒有忘記這句話。遇到很感動我的書或藝術作品、電影、音樂時,我的心裡依然常會輕柔但清晰地浮現這句話。
陳:從第一部短篇小說《敲昏鯨魚》,到這本《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時隔12年,對個人創作是否有不同的要求?
包:我想我很希望這本小說有一種做夢那樣的質地。不是那種從高處墜落,突然驚醒,發現數學老師正在講台上瞪著自己的那種夢,是那種很悠緩、真實、每個節拍、轉場與銜接都自自然然的,彷彿打定主意不要去驚擾做夢的人,的那種夢……是醒來之後人們還會在床上望著天光怔忡許久,回想著剛剛那是夢嗎?的那種夢。
我很希望寫一篇那樣的小說,像我小時候讀過的漢聲青少年拇指文庫的小說,《紅色羊齒草的故鄉》、《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第十八號緊急措施》……那樣的在我讀完書,闔上書頁好久以後,都還是覺得書中世界的質感栩栩如真地留在我的膚觸上的小說。會在恍惚的瞬刻讓我感到夢與現實與書中的世界彷彿並無差異的小說。對我來說那樣的小說有一個內部,有一個可以棲身的空間。我想創造那樣的小說。創造那樣的小說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準則是:不要打擾做夢的人。在夢裡,一切舉措都要輕柔一些。在寫這篇小說時,我把很大一部分的心思放在這個準則上。
* 感謝陳素芳總編與包冠涵協力參與!
↳ 各式酷照片與圖說為包冠涵提供 ↳ 雙人合照(左)陳素芳總編(右)包冠涵
* 各式生活照片與圖說皆為包冠涵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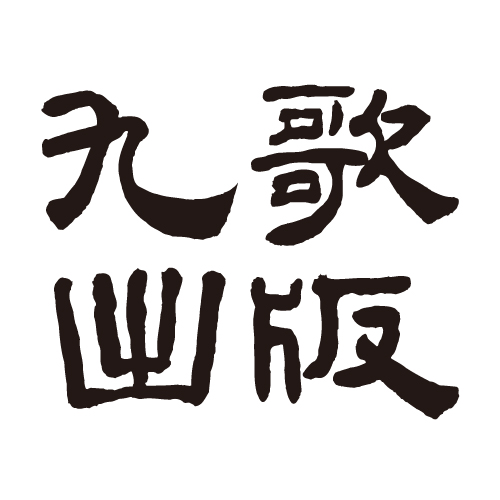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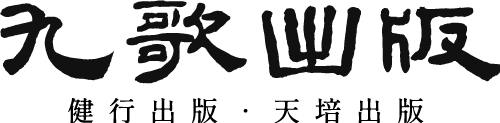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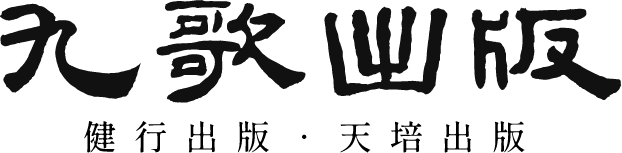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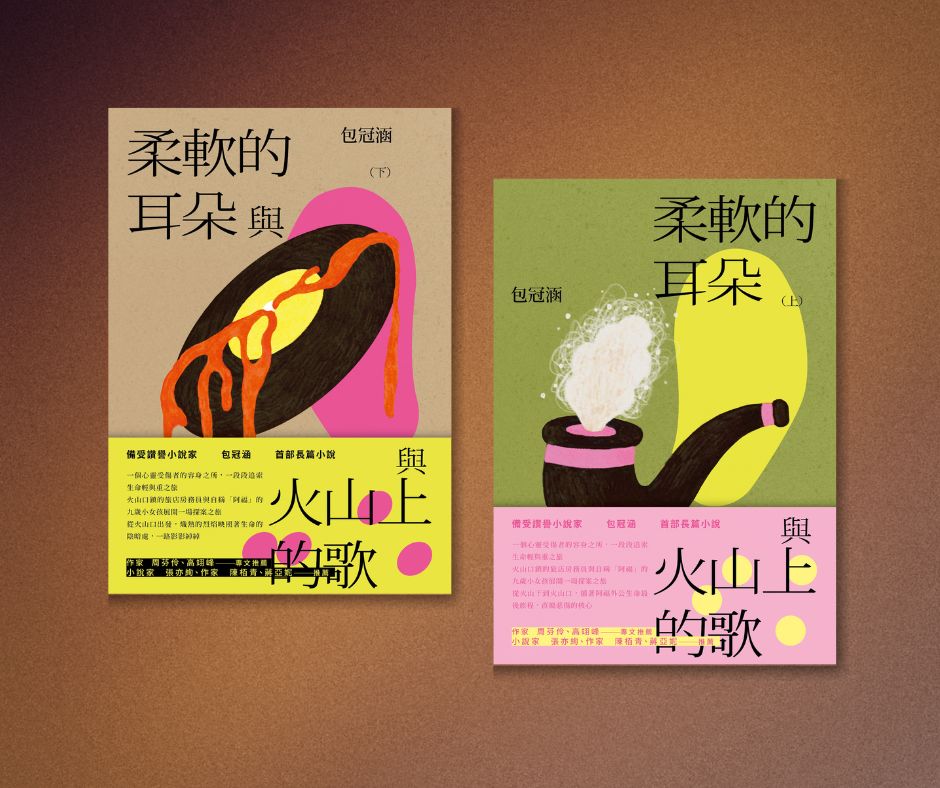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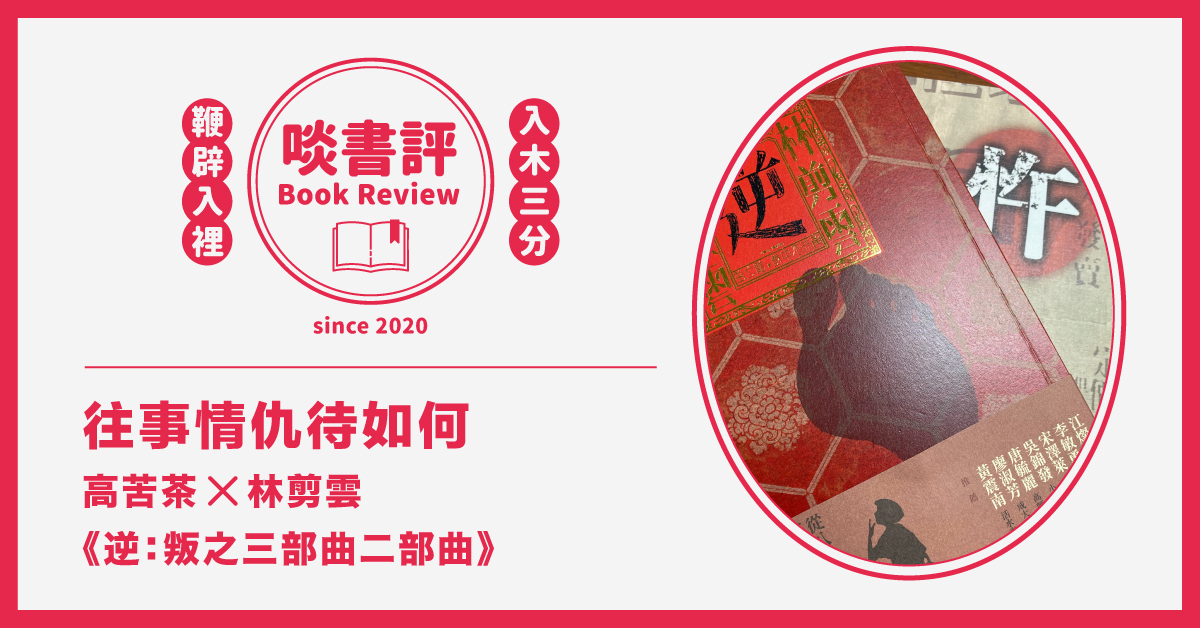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