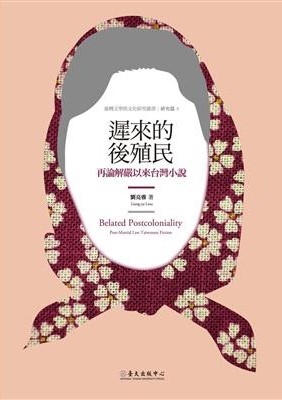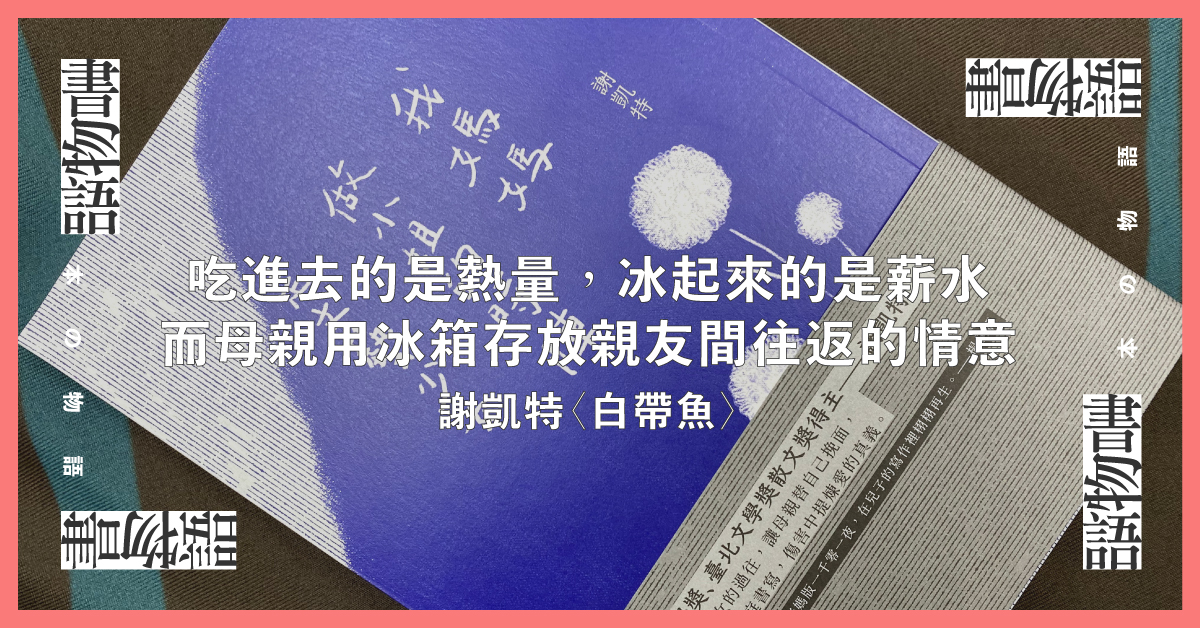解嚴後臺灣囝仔的三合院創作課:劉亮雅、楊富閔對談(上)
由臺灣文學學會與國家圖書館主辦之「2020夏季閱讀講座:集結,千禧世代作家:新世代作家圖像」講座,今年五月下旬於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三樓國際會議廳盛大展開,而本場次〈解嚴後臺灣囝仔的三合院創作課〉即為系列講座之一。主講人為小說家楊富閔、與談人為國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劉亮雅。本場次並於七月四日圓滿落幕。本文即為該場講座精彩的對談紀錄。內容經由主講人楊富閔與劉亮雅教授修訂完成。
劉亮雅:
我想先從你的創作背景談起。你非常早熟、早慧,從九○年代末期開始,就有自己的創作。大學時獲得多項文學獎,到目前為止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六本散文集,相當多產,也相當叫好叫座。你的短篇小說集《花甲男孩》改編為公共電視植劇場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是當時植劇場收視最高的劇集;之後又改編為電影,如果我記的沒錯,電影賣了一億。你的散文集《我的媽媽欠栽培》被改編為臺灣歌劇,這些跨界的改編在在顯示你的作品所獲得的廣泛共鳴和巨大迴響。我的第一個問題想要問你,你覺得改編有忠於原作嗎?你怎麼看待改編與原作的關係?你參與了改編之後,會想要未來與某個導演合作撰寫原創劇本嗎?還是你想繼續寫小說、散文?
楊富閔:
這幾年來我的作品開始有了跨界改編的機會,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收穫,即是重新定錨「作者」此一形象,它在此一故事的流變與轉譯之中,它的角色意義是什麼;以及重新去釐清、摸索一個與這些「作品」共處的方式。我會留意到這個面向,主要是我所身處的創作背景是個網路時代,我的生活與網路不可分割,而每天我們都在處理海量的訊息,我們常常在對一個事件進行「轉載」、「瘋傳」或者「截圖」等再詮釋,那也讓我去思考:這個將被改編而出的「我的故事」,它與原著之間,可能產生的種種變化。
「忠於原著」這個問題終將因人而異,而我似乎也只是作品的其中一個讀者。讀者各自去表述這個故事的原委,並與他們的閱讀經驗產生共鳴,我覺得更好玩,我其實花蠻多時間,沉浸在觀眾的留言與回應之中,不管讚許或者批評,我更想知道:我們如何因為這個故事,以這個故事為核心,召喚而出了互不相熟而生在島上的人,彼此特殊的生命經驗與生活方式。所以近些年來,我在這些跨界合作的過程,反而常去觀察故事如何電線走火一般的擦出種種驚喜:原來這個故事可以被這樣解讀、可以被這樣想像,它對影像、聲音、美術等不同專業項目的人,必然有著全然不同的樣貌,所以我覺得自己像是來修課的研究生。我可能還是有一個「守備」的位置。可是更接近一名聽故事的人,藏躲在群眾之中。換言之,改編與原作之間的關係,提供給我更多寫作方法上的啟發,從文字出發,最後還是回到文字,而這也與我近年文字創作的關懷其實遙相呼應。
《花甲男孩》與《我的媽媽欠栽培》是完全不同型態的改編,前者改編成為電視劇、並在網路平臺可以持續反覆收看,也改編成為很「限定」的賀歲片,電視劇同時也有一個漫畫版;《我的媽媽欠栽培》則是一個聲音的實驗,它是一個全本臺語的創作,混合國樂、偶劇、歌仔戲等多重形式而成為一種新的發明,這些都已超出我的能力,我可以做的就是繼續寫新的作品,讓以後的作品持續越界對話,同時又與我的作品產生連動關係。這樣說來,作者對於作品的詮釋空間,是變得更大還是更小?我們大概要回到最初的文學理論、文學概論的世界去找答案了,而這也是二○一八年我在兩本《故事書》試著去想的問題。

劉亮雅:
你是「新鄉土」的代表作家之一。你的新鄉土有許多特色,包括喜感逗趣、濃厚的民俗色彩、鮮活的臺語、細膩呈現庶民生活和情感、不同世代的鄉土記憶、鄉土的變化、對鄉土歷史的關注等等。你是1987年,也就是解嚴那年出生,成長於臺灣民主化、本土化的時期,你對這點也充滿自覺,例如你有兩本散文集《為阿嬤做傻事》和《我的媽媽欠栽培》就以《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為標題,今天對談的標題也有所呼應。《花甲男孩》裡有很強的本土意識。例如〈逼逼〉裡水涼阿嬤是平埔族,強調所有子孫不分新來後到,不分國家都要寫進死去老公的訃聞裡,〈花甲〉裡強調家族在臺灣兩三百年。我想要問你,你的本土意識受到哪些影響?由於本土意識涉及了歷史感,我也想問,文史研究對你寫作生涯的影響,是否有階段性的不同?許多長輩的凋零是否增添你的歷史關懷?
楊富閔:
如果我們以時間當成座標,我是出生在臺灣解嚴的元年一九八七年,這我也很有自覺,媽媽常常告訴我,她挺著大肚子,肚子住著快要出生的我,跑去拉布條大聲公抗議她的罐頭工廠惡性倒閉,而我的童年則是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這個時期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不可能沒有影響到正在長成的我,差別是我用什麼方式去回應。
回到文學創作來說,我成長的鄉村並無所謂的書店,我的文學閱讀必須去到小小的圖書館,其實我的閱讀沒人引領,但也因此非常個人化,我好像在自主學習,自得其樂。二十世紀最後十年,我常在圖書館借閱地方文化局出版的各種鄉誌、調查報告與風土書。當時臺南尚未合併,我住在農業縣臺南縣,我最愛看「南瀛文獻叢書」,這些書太吸引我了,當時我常把一系列以「南瀛」為名的書籍抱回家,最常借的是黃文博老師的《南瀛地名誌》,上面記載的地名,除了有普遍性的用法,也有非常在地的稱呼,這是下過苦功夫的書。我逐一辨識書上寫的,跟我眼前看到的,我的共讀對象則是祖母,我常會念給她聽,她會好驚喜對我說:「這個書也會寫喔?」那些地方常是她少女時期去的偏遠地帶,後來我也常常拿著這些風土書寫,對她進行簡單訪問,這大概是我的一種本土意識的萌發,是從我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踐而來的。
此外,我的喜歡寫作,其實家人沒有察覺,我也無從知道家中是否也有一個與我興趣相投的親人,我要到高中時期才知道我小舅是個文藝青年,長年在外的他,留下一整間的書牆,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五年級野百合世代,他自己也寫一點詩,我曾看到他寫準備存錢要買「臺灣作家全集」這樣的日記,他也有看到我出第一本書,他是在2010年因病過世的。他病後回到臺南老家,常常剪下刊有我的作品的報章雜誌,我寫的〈逼逼〉,即是以外婆家為背景,外婆後來將這些剪報拿給了我。這件事情於我是一個挫傷,我們從來沒有聊過什麼,後來重新回到他的書櫃,當時我也有了自己的文史閱讀心得,我才漸漸重新去認識他。關於小舅,我還想繼續藏在心裡。
另外,我也很崇拜我的二舅公,他有個美譽叫「麻豆活字典」,他是我外婆疼愛的弟弟,長期在地耕耘的文史專家,研究貢獻甚深,我常在臺南看到他撰寫的碑誌。二舅公很熱情,常常寄給我他的自印出版品,他有近三十本的著作,近期也有一本自傳。他的學問是硬功夫,用腳走出來的,在他面前我覺得自己渺小。這樣想來,我好像不是孤單的。所以當我越挖越深,才深掘自己寫作其實剛剛開始,我只是遇到了該遇到的人,知道了需知道的事,而我必須用我的方式去應答。
劉亮雅:
《花甲男孩》是九個不同的短篇,《花甲男孩轉大人》卻是一個家族的故事。而這似乎開啟了《為阿嬤做傻事》和《我的媽媽欠栽培》兩本散文集裡的家族故事。《花甲男孩》裡有些故事滿沉重悲傷的,例如寫到家庭暴力、性別歧視、老一輩紛紛老病、進入安養院呆看著電視螢幕、一場場喪禮、年輕人外移、鄉土衰落、成功者與魯蛇的對比、大家族的問題等等。在電視劇改編以及《為阿嬤做傻事》和《我的媽媽欠栽培》裡其實也有,但比較是以喜劇詼諧或荒謬的筆調加以轉化。所以你的喜劇裡藏著悲傷,悲喜交集,你的鄉土充滿了複雜的禮俗和人際關係。我想要問你,你處理八九○年代鄉土時,抱持的是懷舊抑或批判抑或更複雜的態度?你怎麼看待喜劇與悲劇?
楊富閔:
我是要到求學階段才知道鄉土文學這四個字,而我其實沒有很抗拒以各種關於鄉土的詮釋框架來理解我的作品。在我的閱聽經驗之中,鄉土元素或者小人物的故事,因為與我的生活親近,確實最能吸引到我,我小時候家裡訂的是《民眾日報》,印象中有個鄉土好人好事的欄目,它附著在地方新聞版面之下,我還拿來蒐集剪報。可能我自己也在讀研究所,一天到晚泡在各種論題的思辯交鋒──不管哪個脈絡之下的「鄉土」話題。有時反而給我很多很多的啟發,比如陳培豐教授對於臺灣話文運動的研究,其中涉及文體的討論,他所使用的歌仔冊材料,在文學創作的層面上,讓我覺得非常震動。關於寫作,我所思考的這些那些,原來前人也有諸多類似經驗,這也讓我以後不單只是從一個創作者的角度來看,而會保持一個文史研究的視野,比較整體的看待自己的書寫。所以它是批判或者懷舊呢?我覺得它可能更複雜一點點,但我不能只是滿足於「再現這個複雜」、「凸顯它的多元」。
而劉老師提到關乎喜劇與悲劇的問題,可以從我自身的閱聽經驗來分享:我是個電視兒童,很小擁有自己的小房間,小房間也有一臺小電視,但是爸媽其實給我超大的發揮的空間,(主要是他們工作很忙。)我當時很愛看介紹在地風俗民情的行腳節目:衛視中文臺的《臺灣探險隊》、八大的《勇闖美麗島》、超視的《黃金傳奇》以及三立的很多很多節目。以前還有一個節目叫做《爆走二人組》,就是徒步環島臺灣,每天大家都在追進度。我很神往這樣的生活,整顆心已經隨著製作團隊走進高山走進原野。同時我也看很多豬哥亮的歌廳秀,至今我仍覺得他的主持能力,也就是說故事的功夫,是很了不起很驚人的,其中那些短劇,讓人分不清是悲劇還是喜劇,常常搬演臺灣的奇聞故事與民間傳說,此一表演形式,可以放到一個更大視野,從戰前到戰後,是有一個涉及語言聲音的脈絡隱然浮現,而他深深啟發了以後選擇使用文字書寫的我。
另,陳玉勳導演的經典國片《熱帶魚》是念念不忘的作品,到現在還是愛到不行,我覺得跟文英阿姨的口音腔調很有關係,她在《熱帶魚》的每句對白,即便只是一個發語詞都有戲,只是那些笑點是如何發生,而讓我們覺得這是「渾然天成」的呢?我常跟學生說,那些曾經讓你愛到不行、並且主動去延伸研究的,大概都是戳到了你的美感神經,非常珍貴,不要錯過,抓住這個感覺,要繼續追下去。

劉亮雅:
家族人際網絡是你的核心關懷之一,你對親子、祖孫關係的呈現深刻動人。《花甲男孩》裡〈有鬼〉、〈暝哪會這呢長〉等故事裡暗示相較於被家族綑綁,那些離家在外流浪或在網路上流浪的人其實是無根、失落,他們的言談背後沒有歷史襯底,失去主體。然而當然也有一些人物是不得不離家逃家的。我想要問你,在處理祖孫之情、親子之情以及處理父權制度問題之間你是否曾遇到兩難?為什麼在〈有鬼〉、〈暝哪會這呢長〉裡最後剩下的是女人為主?
楊富閔:
這本小說寫於十年之前。十年之間我又寫了不少作品。當年我的解法與現在我的解法,不知道有沒有改變。我成長在一個楊姓大家族,老家隔壁還有一間古厝,近日剛剛成為暫定古蹟。〈有鬼〉是我的第一篇小說,〈暝哪會這呢長〉是我比較常被收錄在選集的作品:前者處理的是逃家的母女同時帶走一尊故鄉的菩薩,後者則是一個祖孫三人住在三合院之間,被各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大內」隔絕而出一個小天地,他們住在那個世界之中,也住在危機之中。聚焦女性與我的生命經驗應該很有關聯,其中家族之中,我最親近的都是女性長輩,曾祖母與祖母影響最深。而無論是小說寫的,或者生命經驗的,女性形象確實更為強悍,我們庄頭還曾有過一支女性組成的宋江隊伍,這在民國六十年代相當特殊。
我的曾祖母是名百歲人瑞,她到百歲之前都堅持獨來獨往,我常在各種演講場合講述她的生命史,我常說她才是我的文學啟蒙,一個不識字的、生於民國前十二年、十九世紀末的老婆婆──而我小學六年,聽令於祖母,要我一天到晚要去注意曾祖母的起居安危,有了更多親身接近她的機會;而祖母因為與我共居一間樓厝,她是一名單親媽媽,而我是善於聽她說話的孫子,我們的情感型態與曾祖母不太相同,更糾葛、更接近現實的生活。這兩位女性為我示範生命的姿勢、活著的方法。
我其實越來越覺得寫作於我來說,其實就是為了「生存」,是精神上的生存,但我也在鬻文為生。我覺得對金錢坦白,與對文字坦白,一樣重要。而這些女性人物,關於生存的各種抉擇,連帶使我在文字創作之中,專注對於女性人物的刻畫。關於兩難,我想到作品中的男性未必缺席,未必是父不詳,更未必是去勢的,尤其一但涉及到了民俗書寫,其中的分工,那些很儀式性的、很線性的敘事,老師提及的父權制度的問題,確實存在許多商榷的空間──〈暝哪會這呢長〉的最後,敘事者我假寐補眠的地方,是祖先雲集且象徵權力中心的神明廳、〈逼逼〉這個故事的操盤手是在電腦前面追蹤阿嬤路線的小孫子,後來寫《故事書》一系列的土地書,我常非常驚恐的發現,怎麼田野之間,只剩下我自己在言志與抒情呢?而這就是寫作很迷人的地方,我在「發現」也在「發明」。我以為原是那樣,寫出來是另一個狀態。內心不停地在開檢討會。
劉亮雅:
《花甲男孩》裡除了很多民俗傳統,也描寫了網路即時通、部落格、流行歌曲專輯、手機、DV、追逐明星、學英文等新世代的經驗。比較特別的是,有些故事描寫從網路下載〈天上聖母禮讚〉、〈大悲咒〉、〈往生咒〉,從網路學習七星步。《花甲男孩》裡有一篇〈唱歌乎你聽〉描寫喪偶的老阿公迷上了電臺的點歌節目,和一群不認識的朋友在空中相會,分享臺語歌曲。《我的媽媽欠栽培》裡描寫全家一起看豬哥亮,描寫母親因為看鄉土劇而參加王識賢的影迷會以及王識賢高唱臺語歌曲時的熱烈場面。我想要問你,你是否有意識地想要描寫老靈魂如何借用視覺、聽覺等新媒介,延續、發展臺語文化?是否想呈現網路可以有助於本土文化的傳播?
楊富閔:
這題可以連帶談談我的語言環境。原生家庭日常講的都是臺語,八點檔看的也是臺語連續劇,我小學時期買的錄音帶都是臺語歌曲,以前三立有個歌唱節目叫做「新人歌唱排行榜」,我學會唱很多臺語歌。我小學時期在學校下課說得也是臺語,國一的時候被派去參加國語文競賽──但我比的是母語演講比賽,因為我被私薦,同學跑去跟老師說,楊富閔很會講臺語。去年中央社集結出版一本書《做伙走臺步:疼入心肝的24堂臺語課》,有收錄一篇我的訪問,可以說是我對此一論題的思考。說臺語這件事其實就是我的生活,它也是我的思考方式之一。
我這幾年最常被問到關於臺語的問題,是如使用漢字去明狀這個「聲音」。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如何以有限文字去明狀那個無限的、想像的世界的。後來我找到一個很好的例子。我說:大家現在都會拍片,手機隨手按了就能錄影,不管是不是有意識的拍攝,現在不妨來個街訪或者田野,或者你就自言自語吧,你會錄到人在說話,各種語言交錯其中。我說,現在這不是獨屬創作者的功課了,這就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你不是在寫小說、寫散文,你只是拍了影像,而你練習替這個影像上個字幕──這個上字幕的過程,勢必讓你超級「有感」,我要如何去明狀這些聲音呢?
記得我跟學生說完,大家紛紛會心一笑。我們現在使用通訊軟體,網紅拍得影片,幾乎每天也在上演這場字幕組的創作課,而各種圖像化、諧音化、自創字紛紛出籠,語言洪流挾著飛沙走石滾滾而來,我後來形容自己的創作更像是一門「字幕組創作課」,而文體是我們的集音器,我要做的,是更細心且認真地去辨識我所聽到的聲音。

訪談下集:解嚴後臺灣囝仔的三合院創作課:劉亮雅、楊富閔對談(下)
|楊富閔
1987年生,臺南人,臺大臺文所碩士班畢業,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目前為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臺大中文系、清大中文系與東吳中文系兼任教師。作品計有《花甲男孩》、《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休書─我的臺南戶外寫作生活》、《書店本事:在你心中的那些書店》、《故事書:福地福人居》、《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編選《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與梅家玲、鍾秩維合編)。作品曾獲改編電視、電影、漫畫、歌劇。
|劉亮雅
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碩士,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任臺大外文系特聘教授、臺大臺文所合聘教授。曾擔任2006-2008年臺大外文系主任。主要研究臺灣當代文學與文化、英美二十世紀文學、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理論、同志理論。著有《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2014),《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2006),《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2001),《慾望更衣室:情色小說的政治與美學》(1998),Race,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 Sula, Song of Solomon, and Beloved (2000)。與人合著《臺灣小說史論》(2007);主編、導讀《同志研究》(2010)。曾編譯、導讀《吳爾芙讀本》(1987),導讀、審定《海明威》(1999)、《康拉德》(2000)、《吳爾芙》(2000),導讀《簡愛》(2013)。

《賀新郎:楊富閔自選集》
作者:楊富閔
《賀新郎》選錄楊富閔文學歷程的代表作品十七篇,一方面帶領讀者穿越楊富閔十年以來的文業長廊;與此同時,透過打散重編,全書除了宛如為一則全新的長篇故事,亦彰顯了楊富閔文學的另類視野,也是楊富閔對於「當代」/「文學」的提問與回應。全書一氣呵成,充滿作者對於文體追求、形式摸索,乃至內容生產的繁雜思考,而文學創作的基本單位──語言文字,則是選集收錄的美學準則。《賀新郎:楊富閔自選集》更是一份來自富閔的文學契書,對於文學創作的超前部署,熱情預約臺灣文學的下一個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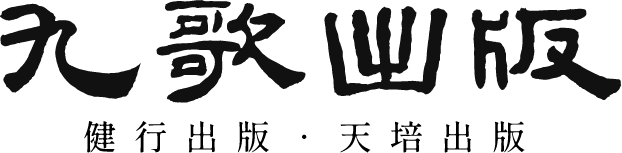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