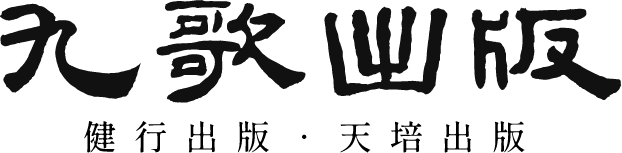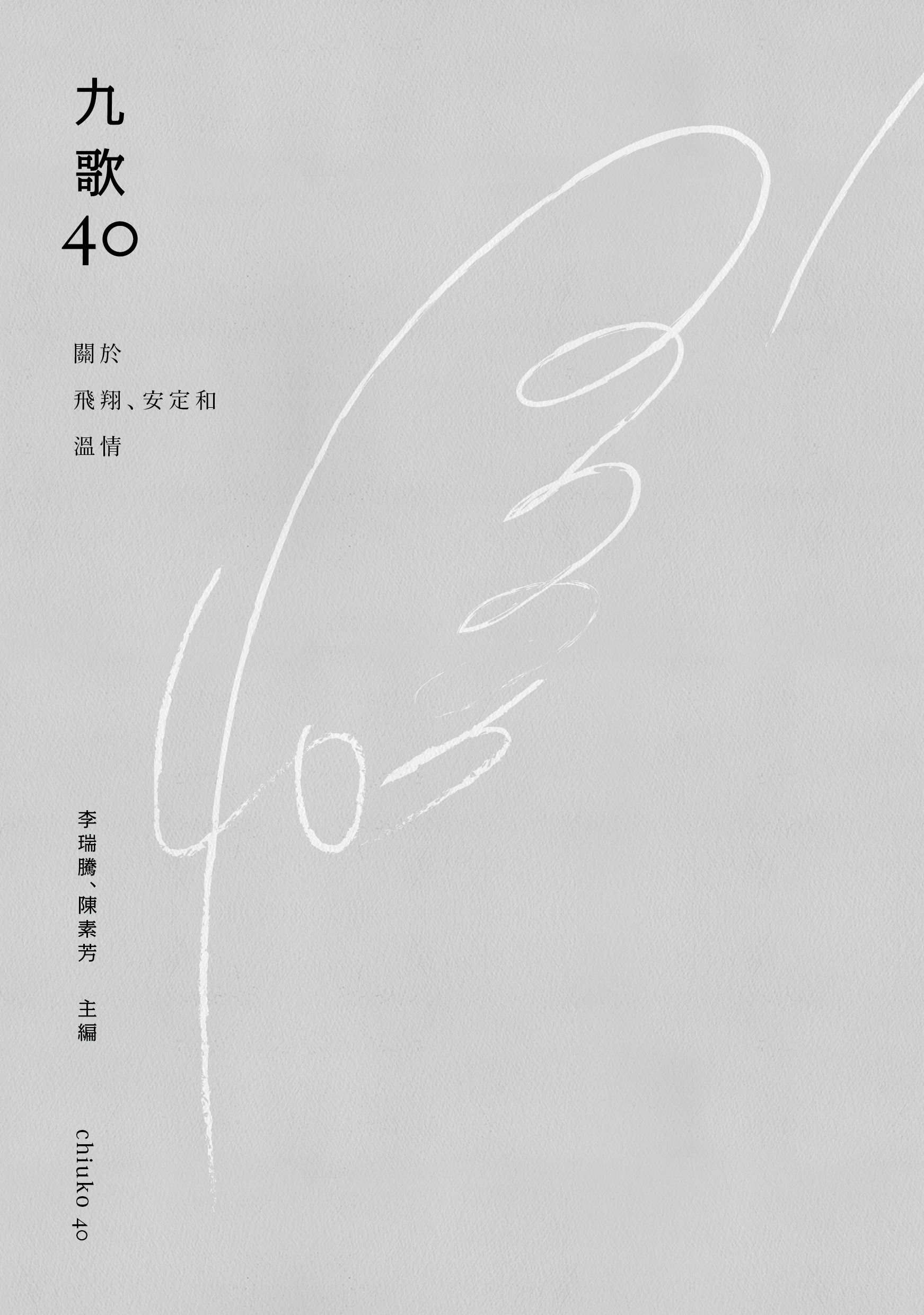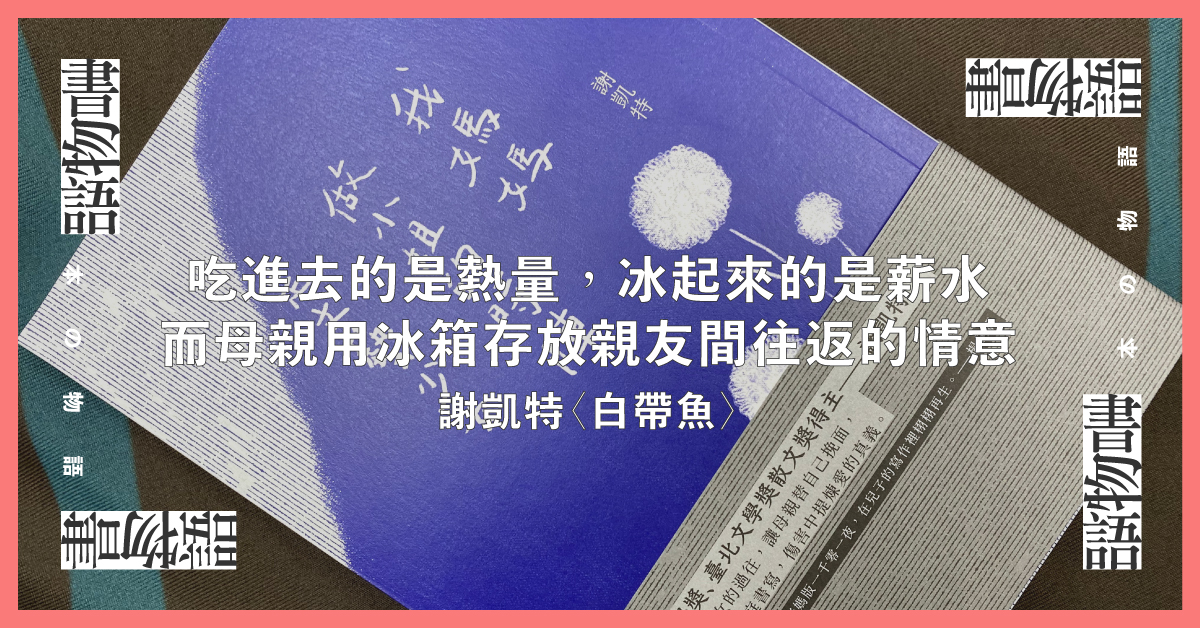言叔夏〈劃撥單的遠方〉
開始寫作以後有許多年,這些蟬翼般的書頁,在行李箱的夾層裡,和我去過了不遠不近的幾個遠方。童年時的我必不知道,寫作究竟可以將我帶得多遠,遠至地平線看不見的彼端,直到所來的故鄉,都變成盡頭的海市蜃樓。
劃撥單的遠方/言叔夏
前幾年出書時,第一次去了九歌位在八德路巷弄裡的出版社。從淡水線轉板南線,在忠孝敦化長長的地下甬道裡,邊對著出口號碼,手扶梯攀升,有點訝異這以一歷時彌久之綠書背、於書店低調示人之老出版社,竟坐落於此繁華地(它不是理應位於冬日的古亭抑或麗水街等城南一帶?)。實則我移居北城多年,卻極少踏入此區,更少在白日掠經此地。上午十點鐘的尷尬時間,夜裡光影交錯的人臉忽而大片消失了,街廓空曠到不可思議。沿八德路拐進的細小巷子裡,陰天早晨的城市微微地轉身,裸露出兩側公寓的岩礫與溝紋。據說舊台視離此地亦不遠,腦中不知怎地,浮出的竟是白光葛蘭從陽台探頭之臉(且梳著波浪髻)。
學生時代常讀九歌,不是因為偏好其出版物,而實是它太易跨過城市與鄉村的某條虛擬曖昧的文化界線,將綠書背地毯般地鋪得綿密且長。即使在我童年老家附近一尋常書局(大量販售文具、禮品的老式書局),仍有一排書櫃,經年累月地賣著一本兩本的琦君與杏林子。推著金邊鏡框的書局老闆可能並不識文學之奧義,卻能細數琦君的橘子是否紅了。想來我對文學最初的想像,也是從這樣的一小櫃書開始:那是放課後的空疏午後,架上的書是一口井,可以讓人將自己埋藏起來;大雄式地(是的就是那位大雄)將書店裡的整櫃書看完,就有一種到過遠方的錯覺。書裡的人在遠方站得小小地。而所謂的遠方,究竟是哪裡呢?鄉下書店書進得少,於是日久我會央母親幫我去劃撥一本循著書末廣告頁的書目清單看來的書名;劃撥號碼一長串,把肚子貼在涼涼的郵局櫃台上時,劃撥單上紅框框的備註欄我想寫上:遠方的朋友您好,我也想看這本書……
多年以後踏進學院,正是網路時代的攀峰之際,出版社的戰國時代末期,各式書背摩斯密碼般地在架上交談,黃書背多當代作者,紅書背凋金碎玉。九歌的綠色書背倒是安靜地潛沉進書架的底處,像是深海藻類。偶然拿出來摩挲,指尖便有一種初衷之感。比如曾麗華的《旅途冰涼》(啊現在還有用聲音在寫作散文的人了嗎?),藏它多年仍剔透如玉。作者少寫,數十年來只成書兩部,一部洪範,另一部即是九歌,都是薄得像蟬翼的小開本。封面設計老式,以致即使從書店買來的新書也像是舊書。
開始寫作以後有許多年,這些蟬翼般的書頁,在行李箱的夾層裡,和我去過了不遠不近的幾個遠方。童年時的我必不知道,寫作究竟可以將我帶得多遠,遠至地平線看不見的彼端,直到所來的故鄉,都變成盡頭的海市蜃樓。但第一次真正拜訪九歌時,有個神祕的瞬間,我卻忽然理解,關於書寫裡的遠方,還有所謂的「命運」,究竟是怎樣的一件事了。或許是因為東區巷弄裡民家一般的出版社,讓人有了這樣的錯覺。又或許是初夏的巷弄,靜謐得像是與它原本的時空脫離。等待門開以前,無意間我仰頭望向二樓時,不知怎地,首先浮上心頭的竟是那張童年的紅色劃撥單。不知許多許多年以前,這二樓窗口的某人是否也收到那備註欄上的話了?也許也曾在心裡這樣回覆我:遠方的朋友您好,您想看的書如下……如果可以,真想問他,那時的天氣好嗎?九○年代,或者,八○年代的天空,都是藍得要刺穿人的顏色。其實寫作的路上或免旅途冰涼,必須幾經跋涉與繞路;而我最初的字,或許早已先於我的書稿,被寄到這裡來過了。
作者簡介:言叔夏
一九八二年生。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臺北文學獎、花蓮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小說獎、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等獎項。著有散文集︽白馬走過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