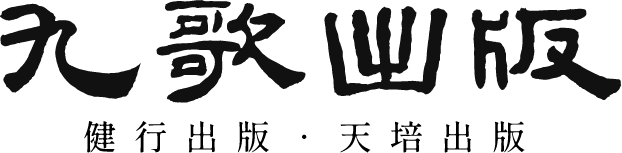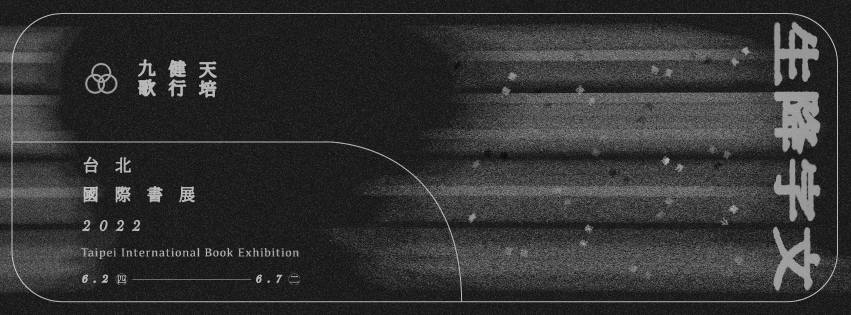注定要被這城市每日新長出的植被所覆沒——言叔夏《沒有的生活》
記不得那清晨入睡、午後轉醒的日子,究竟是從我年輕時代的什麼時候開始養起的。像養大一個孩子那樣地,白晝的日子漸漸矮小,夜晚慢慢長高。直到後來,照鏡子的時候,我就忽然有了一個臉面漆黑的孩子,陰影般地黏附在我的面孔上。像是夜晚的胎記。那奇怪的惡習起源,如今是怎樣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閒散無課的大四時代,我幾乎是把一整年的白天給大肆睡掉的。這個惡習持續到了研究所時代,至今仍跟隨著我,使我在亮晃晃的白日底下走路,都感覺背負著一團黑色的影子。有段時間我背著這團黑小人到事務所去,工作,排隊,辦事。感覺五臟六腑都疼痛了起來。
別人並不知道你背上的這團黑影子,只當是這個城市慣常陰霾的天氣。誰也不在意誰的心緒。可是那黑小人煙霧一樣地阻隔在你與他人的話語之間,遂使那話語聲響底下的意義,都三角鐵的尾音般地分岔了。白日裡的世界持續運轉,並不會因為你的作息而調整。於是我的掛號信件被耽誤,且永遠無法在郵局開張的時間去領取,工作電話始終接不到,下午茶失約(日久遂漸漸沒人在這時間約你出來談事吃食),醒來時圖書館常已趨近關門。夜晚我像小偷一樣地搬運那一綑又一綑逾期的書到圖書館去,一本一本地將它們餵給還書箱吃。因為每日都是由每個半日組成,我老是搞不清楚怎麼理解「今天」這個詞彙。午夜十二點過後,究竟該算在今天還是明天的帳上?於是在深夜回覆那些信件匣裡耽誤的郵件,鍵盤敲打到「今天」這個詞時,總有一種忽然陷掉進日子夾層的迷宮之感。
蟄居河邊的老舊公寓時,這樣的惡習達到了極致。學位論文寫到擱淺。我日日坐在陽臺對河發呆,唱歌,想念一些遙遠的人,為著不著邊際的事物哭泣。今天與明天的交界模糊,輕易地就被午夜給跨越了。那時我最常拜訪的是橋邊的便利商店。有三個圓臉蛋的胖店員總是輪流值著午夜的夜班。因為長相的緣故,我總分不清她們其中的任何一個人。因那木柵深處的深夜裡什麼吃食也沒有,那便利商店架上的便當與麵包便被我一季吃過了好幾輪。我那長時未修剪的一頭亂髮紮成一條凌亂的馬尾,戴深黑色大近視眼鏡,拖一雙陳年破爛老勃肯鞋,出得門去,在凌晨三點的斑馬線上旋轉著過馬路。感覺一種踐踏,同時又在踐踏裡感到一種揮霍的自由。
那樣的自由是無可言喻的。是雙腳穩穩踩踏在一條安靜的路上,傾聽鞋尖踩踏著整路哐啷哐啷碎石子聲響的自由。不是人生裡任一由金錢、學業、工作與飛行里程航數堆積起來的數字所能比擬。沒有信件。沒有旅行。沒有多餘的話語與交談。只有日復一日流淌過陽臺下的河流,在夏季颱風來時倏忽地暴漲,在冬日裡乾涸。
日子久了我漸漸理解這樣的生活其實無異於盆栽。沒有長大的野心,也沒有換盆的願望。在一般人眼底,它甚至顯得乏善可陳,沒有過多關於文學的浪漫想像。因為過短的白日生活,我幾乎不上咖啡館,不去書店與電影院,不在房子以外的任何一處讀書寫作。離寫作最近的大概是放空,大量的放空,在漫長的白日裡我把自己放置成一個空空的容器,什麼東西都裝得進來,卻什麼東西也都沒有裝盛。那樣的生活是由大量的「沒有」所堆疊出來的。而因為這許多的「沒有」,我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真正地感覺過自己的富有。
在這個城市裡,有多少人和我一樣過著這種「沒有」的富有生活呢?我想起住在那老舊公寓時的一個女學生鄰居。很少出門。戴著圓圓的近視眼鏡。很是文靜的樣子。那個房間在我租賃下這裡時曾經被房東帶進去看過,是一個沒有窗戶的密閉空間。她搬進去以後沒有多久,我老是在深夜的走廊上,看到她的門口擺放著喝完的水果酒空罐。那個罐子的擺法非常含蓄,像手指緊緊併攏地貼在牆角,而且從沒有擺放超過一罐過。那不是為了悲傷或煩悶而喝的酒。那是一日一瓶,像盆栽植物那樣澆灌自己的水酒。
這樣「沒有的生活」,在告別了學生時代、進入白日的工作以後,被很物理性地轉換成另一種形式。博士班的最後幾年,因為工作的緣故,我搬離了那河邊的老公寓,移居到城中的另一座樓。那樓在喧鬧的捷運站旁,兩側皆是儼然的寫字樓。只有一幢兩層樓的破舊屋子,極不搭嘎地坐落在大樓與大樓的中間。那屋子的騎樓有一棵年老而巨大的樹,長進了騎樓天花板的屋裡,在屋頂竄冒出樹冠來,像極了那屋子頭上戴的一頂假髮,被四周的公寓大樓環視著。屋子的一樓其實是一家尋常便當店。午後便當屋的鐵門拉下半掩休眠,像把整家店都收進了那樹的肚子裡。
有一日的傍晚散步途中,途經那旁側的大樓,底下聚攏了人群。還有幾臺電視臺的採訪車。幾日以後我才在深夜重播的電視新聞裡,看到了熟悉的街景,還有便當店夫婦哭泣的臉。是他們親近的誰的孩子從附近的大樓失足掉了下去了罷。是一個夾雜在一日的各種災難之中,很快地就被沖洗掉的微小事件。我感到在那一、兩分鐘的新聞播報裡,有些什麼曾經離我非常靠近,卻明確地知道它早已真切地是十分遙遠了。我想起有段時間那便當屋確實默默地關上了幾天。在白晃晃的夏日豔陽底下,遠處傳來修路工程的喀啦喀啦聲響。空氣裡有新鋪的柏油氣味。我踩踏著一條日復一日的黃昏巷道,去買回重複而無聊的吃食。像一隻貓舔毛般地將那些食物緩慢地吃完。整理自己分岔的毛髮。
那是他人之死。他人的日常。他人持續的人生。如同我的。然後,在某年的夏天結束以後,我就搬離了那座樓,帶著我那其實一無所有的老舊家具,不來梅吹笛手般地到另一個城市去了。像一個注定要被這城市每日新長出的植被所覆沒的故事,包括我曾以為我在這裡活過的證明。沒有什麼被留下。什麼也沒有。
── 原文〈沒有的生活〉摘自言叔夏同名散文集《沒有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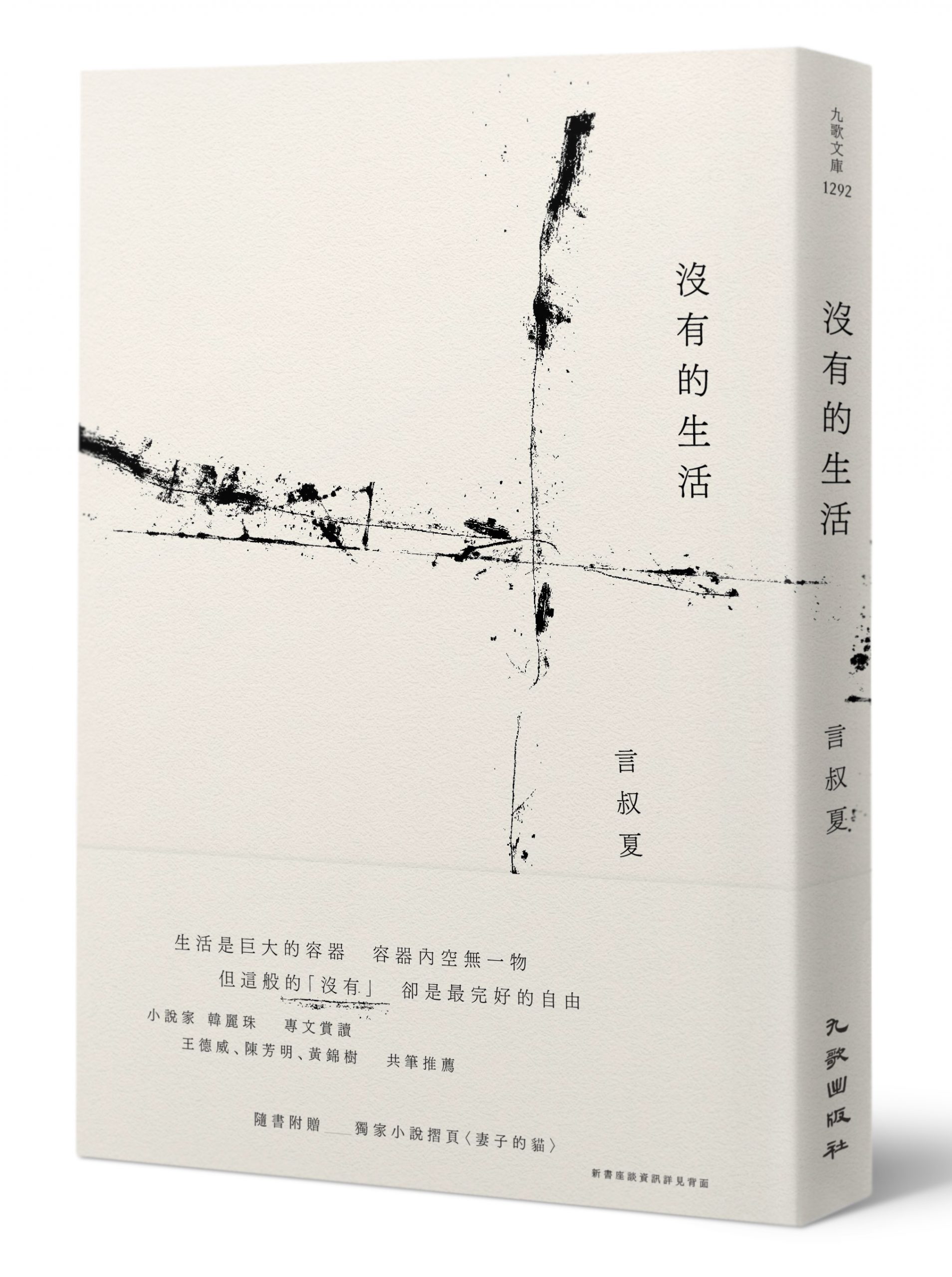
|言叔夏
一九八二年生於高雄。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東海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九歌年度散文獎。著有散文集《白馬走過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