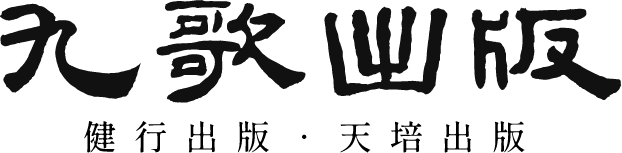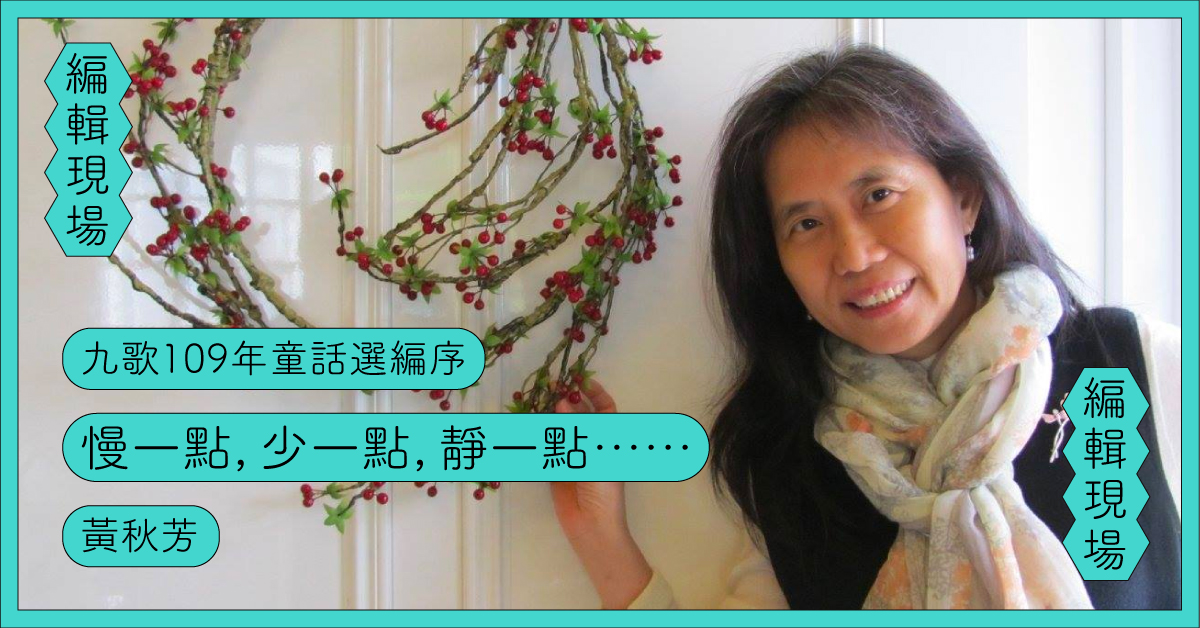玖芎的女版「野孩子」 :張亦絢《我把自己埋進土裡》推薦序
《我把自己埋進土裡》是玖芎以女身經驗出發,從親族私隱、成長暴力、愛戀的摧殘,到離開臺灣至土耳其留學所見的政治、文化、性、愛、異鄉的孤獨,玖芎以尖銳而誠實的筆法,如臟器外翻般,將之一一赤裸寫下──「我把自己埋進土裡」是她親手將自己埋葬的旅程。
玖芎的女版「野孩子」/張亦絢
一九七○年,楚浮拍出《野孩子》。電影根據十八世紀的醫生伊塔爾(Itard)的紀錄改編。儘管是重構,也算是楚浮片單中,少數具有一定真實根據或說紀實性的作品。有回我與外國友人聊起,對方立刻謙道:「人文社科不是我的專長,『野孩子』的主題可能要問社會學學者。」原來「野孩子」或「野丫頭」,並不是我們形容丟丟石頭嚇嚇小貓、不太乖巧的小孩——有人定義「野孩子」也是「在人類社會之外,或邊緣成長過的孩子」。
《野孩子》裡的維特多被發現時,約十二歲。不會說話,長髮披肩,四肢著地前進,有人認為他是白癡。後來對現實中維特多的研究,也有人指出他可能是被虐待或遺棄。楚浮聚焦在伊塔爾與維特多的關係,很可能的原因是,楚浮不只關注兒童,對「重返社會」或「社會融入」有很複雜的體驗。眾所周知,他本人就被關進類似少年感化院的機構中過。伊塔爾辛苦地想要教會維克多說話與作為人類的基本知識,比如睡床不睡地板等——但楚浮並不一味讚賞「人類文明」。有一幕是維特多想要淋雨,那可能是他過去的愉悅,但「被淋濕」卻被「人類常識」不假思索地認為要避免。因為無法教會維特多說話,被當作特殊教育先行者的伊塔爾,認為幫助維特多社會化的努力是失敗的。但楚浮的用意比較不在這部分,反倒是藉由這一章,警惕人們在文明與非文明之間畫界的慣性,是否太過想當然爾?而強制「學習」在什麼水位,會從人性變成反人性?哪些權力關係必須檢討與改變等?才是大哉問。

楚浮《野孩子》預告
進入厚顏系的傳統
我在討論玖芎的《我把自己埋進土裡》的一開始,先想到的「野孩子」概念,比較近於楚浮的——換句話說,「野」就是能感受,所謂規矩、教育、語言表達、社交技巧或泛稱為「人情世故」的東西,並非絕對善或絕對正面。——當它作為使人驚慌失措或得以排斥厭惡他者的「標準」時,它也是恐怖、懲罰與剝奪的化身。這個道理,批判「事物放諸四海皆準」的社會學中,有過許多具體案例的呈現。有個著名的例子是談兒童回答「香蕉顏色是黃或黑」,要看他們社區的超市一向進的是新鮮或快過期的香蕉——並不是智商決定答案,而是生命經驗。如果對這個問題有興趣,《我把自己埋進土裡》中的反覆變奏,絕對會衝擊你心,並帶來超乎預期的收穫。
生命經驗並不是我們能夠坐享其成的東西。在注意到其緊扣並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野孩子」面向之前,最先令我肯定的,是作者在敘述時投入的心力與技巧。它們高度主觀、盡可能準確、並且「毫無繁文縟節」——這種直搗要害的特質,與第一流作家如太宰治、張愛玲或像翁鬧〈天亮前的戀愛故事〉的「不要臉」功力,深深相通。前輩因為已有文名,不可逆地會被某種敬意滲透,有時無形中削弱大家感受他們創作初始中的「pháinn-khuànn-bīn」(歹看面,丟臉)的力量——這也是我們在談論文學時,常要還原之處。但我相信,對於不那麼失憶的讀者而言,辨認出玖芎「厚顏系」的脈絡與成績,應不困難。儘管書中並不旁徵博引,也少秀出閱讀清單,但若非曾經大量閱讀,甚難有書中的布局敏銳與文字功力。我非常讚賞作者不假手理論,不輕用比喻,為其經驗研磨出的第一手敘事——這裡文學性的誠意是滿點的。
玖芎用來處理的「名為我之物」,看似沒有史上的「野孩子」那麼極端——雖然她對「開口」一事情緒複雜,嚴重到曾出現「嚼碎舌頭」這類字眼,使人覺得她幾乎有種「如獸對人」的暗潮洶湧——另方面,她的「野」卻也未必就不艱難。因為所有問題都是內隱的,甚至在一開始是無組織未命名的。渴愛、孤寂、羞恥,誰都感受過,為什麼她似乎「超額擁有」?——稍微總結地說,「她極度沒有安全感」這事,或許對若干讀者也會造成「是否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疑惑。而我也是到了本書的後半部,裡頭提到「如廁習慣」的一句,才有拼圖集成之感:「啊,一切都說得通了。」
率真與褻瀆之必要
我希望大家不要誤會,當我說主述者「沒有安全感」,不是在譴責她或認為她本身有什麼錯。我想強調的是,除了先天性格不同外,童年環境的安穩與否,對長成後處理壓力的方式會有影響。即使當我們聽到「虐待」,也不見得能判斷嚴重性。比如「父母不是非常關心我」,是可以有從「見死不救」到「給我自由」最壞到最好的不同等級。我並不是要做心理分析,但我從中讀到的「忽視」,我認為只要對兒童權益有點認識的人,都不會否認那對兒童會造成的傷害。有些人的父母可能忙於工作或離家在外,這都未必會造成傷害,因為導致兒童不安的,不是父母的物理性不在場,而是精神或象徵性的。——後者的「缺席」,其型態可能是「在家卻冷漠」或「在家但製造混亂」等等,這都是玖芎捕捉到的「她的真實」。我們看到她描寫自己長大後,在衛生主題或生活不真實如電影的段落,必須了解那並非挑起潔癖派與非潔癖派之爭,而是關於她如何進入與理解壓力事件與自我。
生命經驗不會寫在臉上,那是不訴說不敘述,對自己都會飄渺之事。《我把自己埋入土裡》是一本率真之書,同時也是褻瀆之書。這是因為率真本就難以避免褻瀆——褻瀆的範圍除了自己的家庭人生,也包括留學土耳其安哥拉一事——偶爾我讀到若干片段,會半開玩笑哎道:「這是要引起外交紛爭了吧。」——玖芎是真的不用外交辭令。
然而,凡是遇到「涉外事件」,都要稍加考慮觀感的「傳統」,本就是對言論自由的箝制。如果玖芎未來是走向文學而非外交,我想不會有什麼麻煩——君不見夏目漱石筆下的留學生倫敦,還不是煞風景煞到不行。我在巴黎的一個同學也是土耳其女生,偶爾我們會聊土耳其的政治與社會。因此,我知道雖然土耳其有其女權傳承,但玖芎所體驗到的不自由與不平等,絕非空穴來風。玖芎在土耳其的見聞錄,也不符合單純英勇、受害或冷靜的類型,但她想要忠於比較大的自我真實,這樣的嘗試斐然成章,頗值細品——儘管她偶爾會將留學生活貶得一文不值,但讀者仍應會發現,那並非全貌,她學會更有層次地看待異文化與母文化,假以時日,我相信她甚至有可能作為土耳其文學與台灣文學的橋梁——如果這本書的這個部分占比較小,原因不過是它並不適合放在「自我歷險記」的散文結構中。
指認軟弱的堅強證言
最後,我想就書中的兩個「禁忌」各說一點話。首先是,關於「真人真事」。我的觀察就在於暴露幅度與創作意圖的比例原則是否合理。而我的判斷是,玖芎已經有所克制了——之所以會有若干細節露出,都與她要審視自己在人際關係中的自我有關——這與她難以了解父母有一定的相關,因為人的表面和諧無法解答自己成長中看到的欺騙或不合,有些少年男女會因為想了解「人這個東西」進入八大,原因在於八大看似通往「隱藏的裡面」,對外遇者的好奇甚至喜愛,也與此有關。
另一個禁忌,是在十四歲之齡就與成年男性交往一事——其實,更禁忌的事也所在多有。對於在性愛關係中,某些明顯的軟弱,書中隱隱指向「因為我飢不擇食」的假設。我想說的是,鼓勵軟弱並不道德,譴責軟弱並不實際——而「飢不擇食」雖常是嘲笑人的話,我們更有必要的是認識甚至同理「飢餓」,並且採取「非鼓勵非譴責」的第三種態度,也就是更深的了解。也因此,我認為玖芎游離出典型少女的證言,尤其應該被置放在她「求生、指認、尋找自我聲音」的向度上來看——雖然這個野孩子沒有人以教導聾啞人的耐性,對她循循善誘,但她自己教自己,開口說出自己的話——這一層的意義非比尋常,而我們當然應該全心傾聽,並不放棄任何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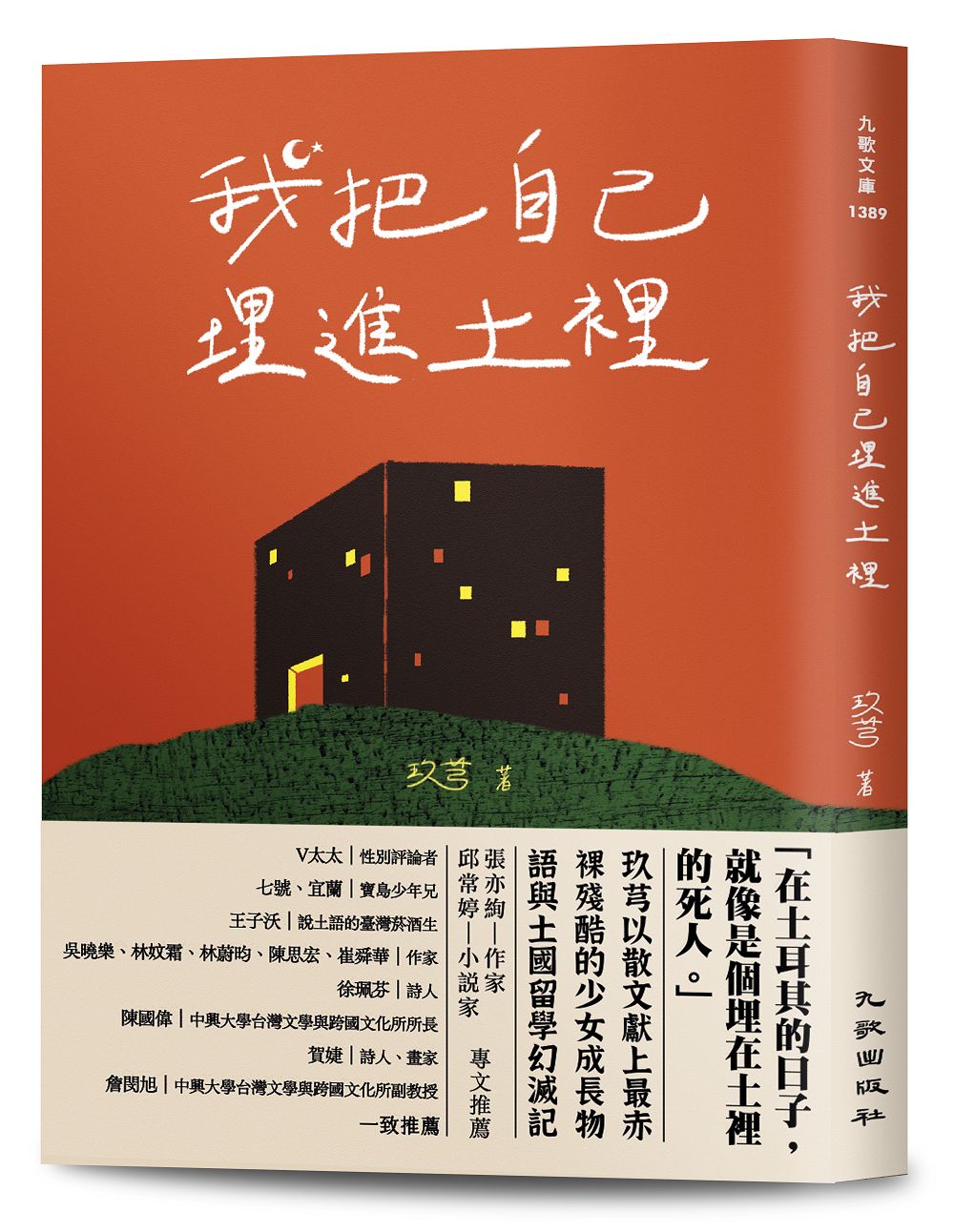
|張亦絢
一九七三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看電影的慾望》,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 /巴黎回憶錄》 (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獲openbook年度好書獎。二〇一九起,在BIOS Monthly撰「麻煩電影一下」專欄。
網站:nathaliechang.wixsite.com/nathalie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