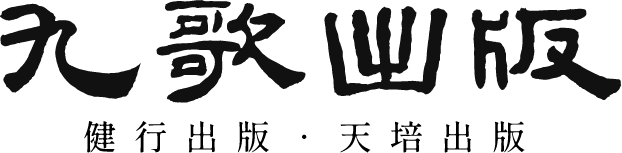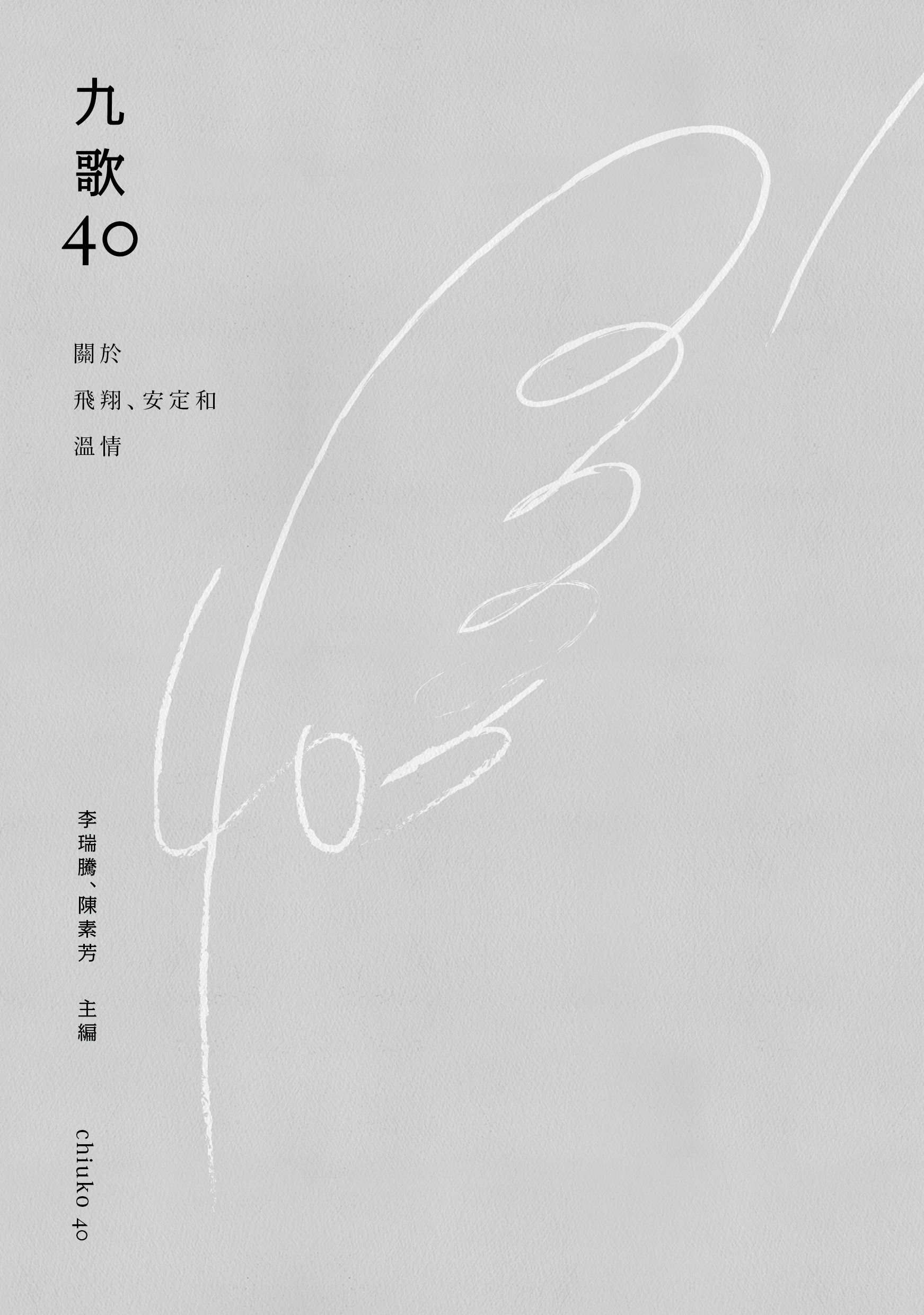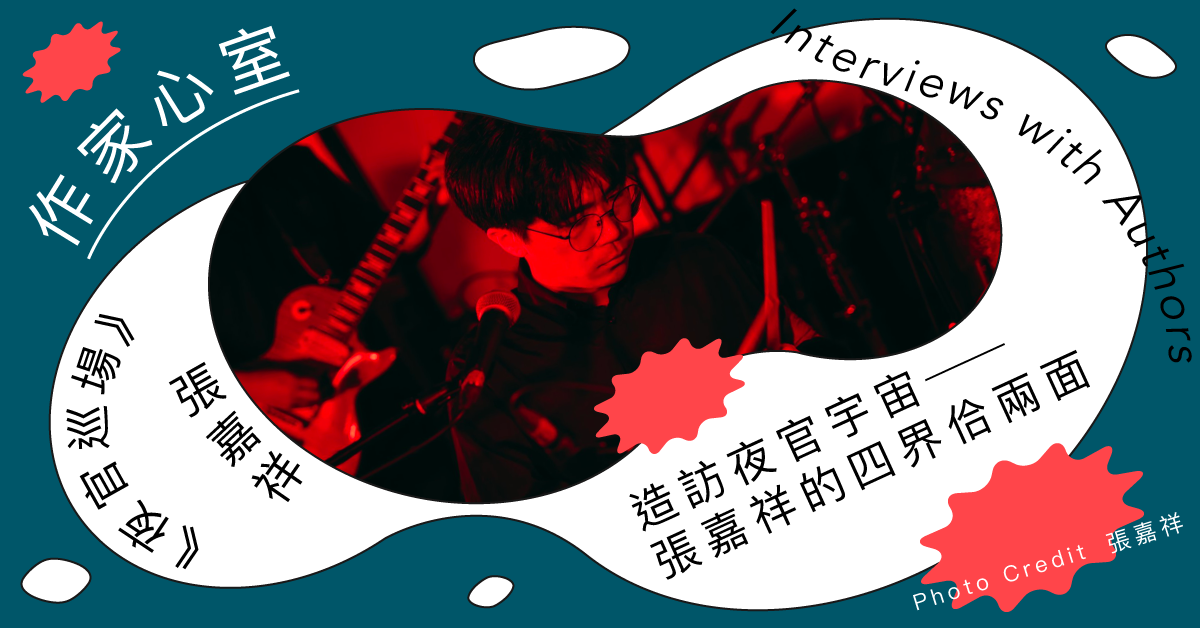朱少麟〈Untitled〉
人生中也許還有更多值得思索的未解之謎,但這隻鴿子撩撥我心的程度不太一般,若說是同情它,似乎貶低了某個神秘又莊嚴的題目,總之我惦記著這隻鴿子,它那種與困境毫不相干的靜默,在我的心裡產生了份量。
Untitled /朱少麟
凌晨三點四十五分,天寒,微雨,我在書房裡,用耳機聽著Mark Knopfler 的吉他曲,The Long Road,大抵上聽過這首歌的人,會承認它有股邪門的力量,能讓人特別沉溺入前塵往事中,這時我想起的,是一隻鴿子。
那隻鴿子,住在台北市某棟危樓的頂樓,那是一個我連在夢裡也不曾回顧過的角落,我也在那頂樓住了一年。
那一年我二十一歲,剛剛離開大學校門,老家在遠方,阮囊羞澀,進退失據,我在市區精華地帶,居然以低價租到了一間雅房,此房就在這棟危樓的頂層加蓋處。
說它是危樓絕不苛薄,電梯早已失靈,二樓以上多半呈廢棄狀態,樓梯間的閃爍燈光永遠提供一種災難電影效果,幾個最陰暗的拐彎處還見得到焚燒過紙錢的殘跡,靜壓過聲,塵多於物,疑似人鬼共居,總要一口氣爬上五樓,我才見得到第一個活人,獨居的女房東,請容我說她也是個適宜驚嚇人的好手,這位中年女士略矮胖,面容恆常睏倦,她喜歡穿著連身的睡衣,在五樓走廊上散步,總是有辦法讓歸來的我與她偶遇,讓我感覺就像誤闖進別人臥褟一樣的不恰當,但我是個太愉快的年輕人,朝她歡樂地揮揮手,我就繼續爬上七樓,回到客宿的雅房。
這七樓原本該是個妝點華麗的空中花園,當時已經繁華謝盡,只剩下一些石雕造景、少數的植物殘樁,還有一圈乾涸的魚池,上面懸著小小一道寂寞的石砌拱橋,魚池旁是四間相連的鐵皮房間,後頭還有公用衛浴間,然而這只佔頂樓一半的幅員,還有另一半的空間,阻檔在一排陳舊的木板隔障之後,那一邊貌似有一棟傾穨的巨大鴿屋。
我是頂樓唯一的租戶。
終於有一天我穿過隔障,證實那邊是個雄偉的鴿屋遺址,至少容得下百來隻鴿子棲身吧,但當時只剩下點點落羽,和大量的鴿糞痕跡,有幾隻鴿子似乎被我驚擾了,撲簌飛走,在天空劃了半個圓,消失,又飛回來,停歇在腐朽的鴿屋門簷上。居處毀了,鴿子還是戀家的吧?我這麼想。
「就我哥啊,他以前愛養賽鴿啊,」女房東煩惱的告訴我:「拜託他好幾年了,也不回來整理。」
直到我更進一步,鑽進鴿屋裡探險那一次,才發現了此生最驚奇的謎團,半毀的鴿屋內有許多小型鐵籠,其中一個鎖死的籠子裡,竟然站著一隻鴿子。
活的,心平氣和的,被關在這被拋棄了好幾年的鐵籠裡,這隻鴿子,對我咕喃了一聲。
我就不叨敘當時是如何一再確認鐵籠毫無出口,如何發現籠內的水盒食槽早已經乾枯崩碎,又如何在與這隻老鴿子對望時禁不住難受。
我給了牠清水與食物,牠不太積極地受用了;我想辦法剪開了鐵籠,牠平靜地選擇留在籠內。
除了屋簷上那幾隻鴿子接濟牠水米、幫助牠活命以外,我完完全全找不到合理的解釋。幾個月後我搬離了這頂樓。
人生中也許還有更多值得思索的未解之謎,但這隻鴿子撩撥我心的程度不太一般,若說是同情它,似乎貶低了某個神秘又莊嚴的題目,總之我惦記著這隻鴿子,它那種與困境毫不相干的靜默,在我的心裡產生了份量。
很多年過去了,我在短暫的寫作期之後又停筆,開始另一種平淡的小生活,某種程度上來說算是佇足不動了,再怎麼摒棄外緣,沒辦法無視的是,遠遠的那頭,有個人始終惦記著我,那是九歌的蔡文甫先生。
因此這時候忽然又想起那隻鴿子,有點巧合,得知九歌正要隆重展開四十週年慶,我想我得從長久隱居中洩露出一些東西,帶著敬意。
回想起來,與九歌結緣,是在它成立二十週年之前不久,當時我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就像個正統的初生之犢一樣,我將原稿掩護在一篇很狂妄的自介信之下,寄送給十幾家出版社,之後是幾個月的苦候,這焦躁結束於蔡先生的一通電話,當時我並不知道承蒙一個出版社負責人親閱稿件是多麼大的榮幸。
記得那是一個深夜,電話那端的蔡先生氣喘吁吁,讓人有種看著他趕路奔來的即視感,他第一句話的耿直程度,是不容許任何作者忘懷的,他說:「妳這個小說是自己寫的,還是抄來的?」
成功地讓我錯愕之後,蔡先生自言自語似的繼續納悶,「不可能啊,從哪可以抄來這麼好的小說?」
當下我明白了兩件事,蔡先生的敏捷語速讓人難以插嘴,還有,絕不能小覷這位長輩對於年輕世代的兼容能力。
簽約,付印,蔡先生親自寫序,親自引領我應付媒體,小說問世後相當順遂,一時間蔡先生贏得了伯樂之名,雖說他早已是資深伯樂,但在那純文學出版物正要式微的時節,他如此提攜一個素人寫作者,對許多人來說幾乎就是暗夜明燈,那幾年裡,蔡先生被指名遞交了好多小說原稿,每當見到他苦笑著示以我又一疊新稿,好像在說「看妳這匹千里馬把我累得啊」,我總有點羞赧之感,千里馬是謬讚,我大約只狂奔了九十里,但蔡先生品賞文章之銳利倒是真,這些年我欠了他一句話,蔡先生,是我沾您的光。
蔡先生寫了文章勉勵我是天生的作家,天生這兩字,對我來說,那意思更傾向於來去皆沒有頭緒,幾年之後,我決定不寫了,短短的寫作生涯中,只與九歌合作,從一而終,我的經驗可能較為侷限,但在這兒我樂意說出一些真心的想法。
與九歌合作的幾年間,我算是個難以照顧的作者,不閱信不應酬,拒絕曝光排斥採訪,這樣倔強的脾氣,在出版社的眼中,想來不算特別,特別的是他們對於一個文壇新人能保有如此高度的寬容,蔡先生的女公子澤松小姐常伴左右,處處守護著出版事宜,令人心安,總編輯陳素芳小姐永遠溫暖支持我的執抝,這些業務上的護持,慢慢發展成近似老友式的相濡以沫,儘管再缺乏經驗,我也明瞭這待遇不太正常。
必需承認,我的確仗著新鮮人的幾分野性,刻意試探出版社的底限,而九歌也有雅量調整接招,雙方就這樣勾引出了一些非典型的相處之道,一切都是為了讓小說問世成功,不是嗎?不只,更因為九歌有敦厚的本質,本質中有個堅持,他們必需呵護能寫之人,即使這呵護已經超越了合約關係,到了超越之處,雙方幾乎締結成了某種親族,我以為這是很自然的,當一個作者,將作品交給了出版社時,雙方不就應該是血脈相連嗎?
事實上我知道這種自然的互相愛護是罕見的,我是很幸運的,幸運之餘,變本加厲,隱居十幾年,將作品的一切後續事宜全推給出版社,九歌溫柔地扛起了經紀人的職務,這些年來依照我意,接洽或阻檔各方探詢,若沒成千,應該也有數百樁勞務了吧,九歌從無抱怨,每當小說又新刷了一版,還要來訊問候勉勵,不盡然關乎利益,這其中有真正的類似於父愛的慈祥,以一個文學出版社來說,我想不出更可愛的形式了。
而最奇特的是,蔡先生始終惦記著我,封筆十二年以來,每隔三年五年,他總要寄來一封親筆函,豪邁的字跡裡,是柔聲的勸請,內容大約都是,少麟,要寫,妳要繼續寫下去。
一家出版社,能讓一個寫作者真心感到虧欠它,這也許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是,四十年了,歷經各種潮流交替,即使不再觀察文壇的我也看出來了,九歌必需因時就勢婉轉調整,但誰也明白,九歌從沒放棄純文學的主旋律。
九歌它,真的成了綿長的歌謠,有部份隨流行,有更多保留了原本的神俊,還始終能押韻。
祝福九歌,謝謝九歌,除了身為穩健的出版社,我想說,您們還成就了某些只能用美學衡量的意義。
|作者簡介:朱少麟
一九六六年出生於台灣嘉義,輔大外文系畢,曾在政治公關公司任職,現專職寫作。其小說以意識流、蒙太奇筆法將主題融入行動中。一九九六年《傷心咖啡店之歌》是她的第一部長篇鉅著,使她一舉成名,自此之後便專心創作,期望能為台灣的中文市場注入新的活力與氣象。一九九九年《燕子》再創佳績,與《傷心咖啡店之歌》並列「最愛一百小說大選」書單,為讀者最期待的作家。睽違六年後的作品《地底三萬呎》也再度震撼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