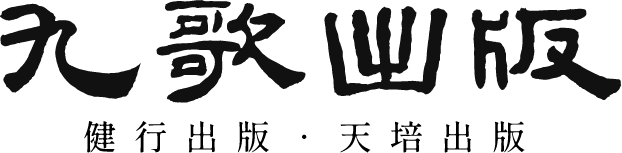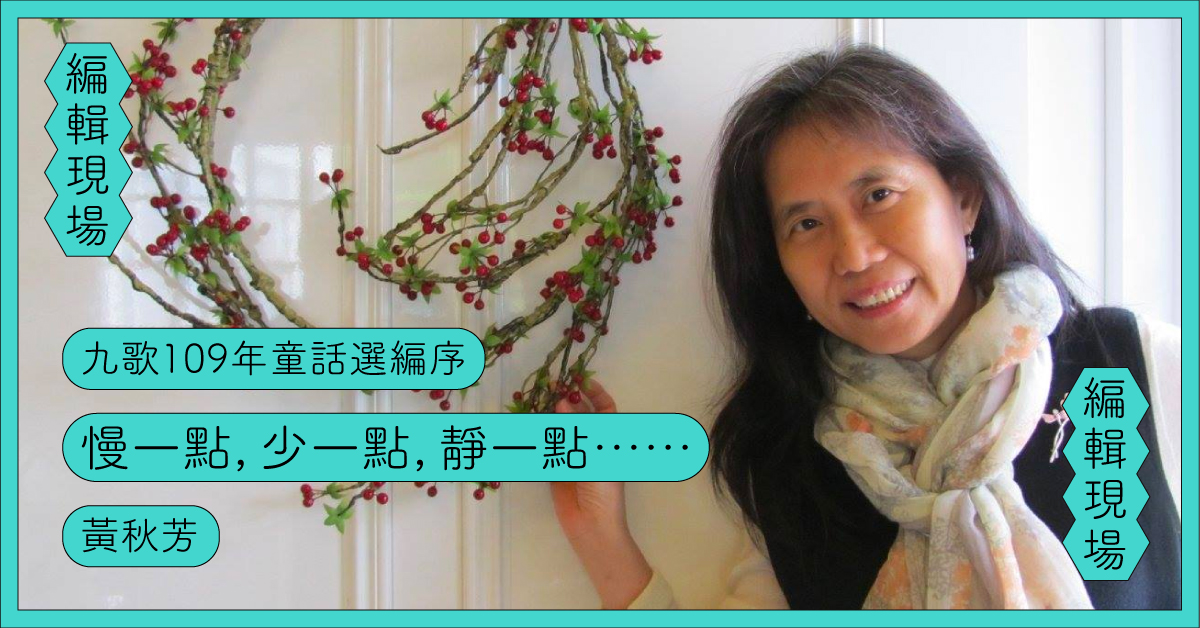賀!這個新郎:楊富閔、許明德的越洋文學對談
許明德:
富閔,讀完這十七篇作品,感覺心中五味雜陳。我想,即使是不熟悉臺南大內的人,都會被你所訴說的生活點滴所打動。你帶領我們從《花甲男孩》的視野,回溯了自己成長的起伏,記錄了自己家族的變化。一方面,囝仔的日常使我心馳神往,有時彷彿真的會看到你和家人在三合院的身影。另一方面,我總覺得隱約有一種悵惘,恰恰因為這種日常太可愛了,總感覺這種生活往往就在消失的邊緣。我想,不如先從你在選擇作品時的心情談起。當你現在回看這些篇章,徘徊在說故事和聽故事之間,你是怎樣看待以往的自己?你寫作時的感受是怎樣的?現在讀自己的篇章時,你的心情有沒有什麼變化?
楊富閔:
這本名為「自選」的集子,以過去十年來的文字創作為收錄範圍。篇目很快就決定好了,甚至早早就在我的腦海,即有一本名為「賀新郎」的自選集等在那裡(2016年這個名字它就出現)。或許從事文學研究的緣故,我喜歡整體性、脈絡式的看待一個作家的從開始到現在,而這本選集於我正是一個節點。篇目底定之後,化身成為讀者,很快我也發現,選集本身的審美準則仍是我最在意的語言文字。這些作品有我對於文體的摸索與追求。編選的時候,不是因為寫了什麼,而更可能是文章體現的文字、語法、觀點,我覺得很有趣;或者文章本身更像一種容器,讓我想起這篇文章,腦袋浮現的其實是一個「載體」,可以仲介而出更多的故事;當然,這十七篇文章,彙整成為一本新書,它將內建一個時間性的敘事理路,我覺得這個理路是文章自己手牽手,自己走出來的。我們可以看到一支空間從三合院出發,時間跨越世紀的失散隊伍,人物散在護龍、無尾巷、芒果園、曾文溪堤,我列隊其中,時而脫隊,時而乖乖排好。有時拿著手機側錄,有時東張西望,有時大開直播,有時就只是隨隊低頭默走。

許明德:
你提到2016年「賀新郎」這三個字就已出現在你的腦海裡了。這書名讓我首先想到的是詞牌的名字。這詞牌背後也是個有趣的故事:傳說蘇軾在錢塘時跟其他人會飲,其中一個歌妓因為沐浴倦睡,所以遲到了。蘇軾於是在席間便為這歌妓填了一首詞,其中有「晚涼新浴」一句,後來就衍生了「賀新涼」這個詞牌。「涼」與「郎」音近,所以後來又從詞牌的名字「賀新涼」變為「賀新郎」了。你當時怎麼會想到取這個書名的呢?
楊富閔:
「賀新郎」三個字很有戲。我想它是戳中我的美感神經,體現平常我在拆解漢字的慣習。首先我喜歡賀這個字,而賀又與台語的「好」同音,賀也可以是個姓氏;新郎則與新人音近,它有性別上的一個頓挫,加上「新人」本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論題,同時「新」在戰前戰後的台灣文史脈絡也是關鍵概念;最重要的是:這是我對自身文字事業的一個冀許。賀新郎三個字可以共構、串流而出許多不同解法。也許這是我的一個人設,啟動以後十年,或者更久的寫作生涯。我對文學其實很有信心,我對未來也是充滿狂喜,到現在我仍會將自己的草稿印出,跑到影片店用最簡便的方式,作成一本如同結案報告的手冊。這是一本限定版的試讀本。接著拿出一枝鉛筆,在一個睡很飽,沒人吵的早上,慢慢看、慢慢改。我覺得這是創作最迷人的時刻。
許明德:
你的作品中有時也會從後設的角度提到創作迷人的地方。〈字幕組創作課〉就是一有趣的例子,其中你從「賣藥仔」一詞出發思考語言風貌和時代精神的關係。這次因為你的選集把不同時期的文章並置在一起,所以我很好奇你自己怎樣看待自己使用語言的方式。這其中是否有什麼變化?
楊富閔:
這篇文章原本收在《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這是我很喜愛的一套概念創作,它也是我對創作方法的一次實踐──我想寫一「種」書,而不是一「本」書。書裡面的文章,可以拿來當成舊作的後記,可以變成未來新書的序文,這套書在我自己的創作路上,它更像一種文學的發明。我很開心完成了不太討好、但可以堅持理念的《故事書:福地福人居》與《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這要感謝九歌支持我的想法。而〈字幕組創作課〉是當中一篇關於創作的宣言。這十年來,接觸到海量的文學史料,發現文學路上我不孤單。我看到一路以來,身在這座島上的文學創作者,他們對於語言文字的豐富思考,以及他們想過、問過、討論過什麼問題。同時知覺漢字文化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再造與變形。台灣的語言真的很熱鬧。其實處在這個內容世代,大家都在祈求一個好故事,但對方法的探究是比較欠缺的。對我來說,反覆丈量自身與文字的距離,納科技於人文,以此形構特殊的創作文論與文體,朝向一種或者多種寫作方法學的建構,是我會鍥而不捨去追問的永恆的命題。

許明德:
你的作品的確常常在探尋新的說故事的方法。〈暝哪會這呢長〉摻合了部落格的內容,也把流行曲帶進敘事裡;《故事書》則收錄了你以往的日記,甚至日曆紙、舊筆記、圖畫作品。我覺得你一直在作許多不同的實驗,我們可以讀到非常一名台灣孩童及其豐饒的內在世界與他的日常生活。而在方法上,你正不停以文字此一媒介,在紙上進行各種的「跨界」,向歷史調度資源,但卻是一個前進的身姿。我特別好奇的是:這與你的台灣文學研究,是否有所關連。
楊富閔:
選擇不同素材豐富文字書寫,自然也在嘗試把文字得以擘劃而出的視域擴大,以此找到更多詮釋與識讀的空間,製造更多媒合與連結的縫隙,用你的話來說,就是探索說故事的方法。或許寫作與研究雙軌並進的緣故,讓我清楚感知:當前對於文學的定義,已經無法滿足於我,我們需要重新去問什麼是文學。就以作家個案研究來說,我很喜歡全集式去理解一個作家,編纂作家年表,加上我又對舊刊物很迷戀,常常重返作家作品的「現場」,我會很想知道他們試過什麼方法,所以作家的文論相也很重要,它與作品本身形成一種對峙的狀態。而作為一個身在台灣的寫作者,我也常提醒自己:還有很多面向要去嘗試,這幾年的跨界經驗,讓我把心完完全全攤開,而我喜歡的作家也都具備跨域的特質。
許明德:
我很喜歡〈為阿嬤做傻事〉一篇,其中你特別提到自己的創作過程:這篇文章早在阿嬤離世前你已開始動筆,但後來完稿時她已經不在。其實除了這篇以外,你在其他的作品裏都會觸及親人亡故的事。我覺得很特別的一點是你在書寫生死的事情上,總能以平靜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哀傷。我想聽聽你怎樣在自己的作品處理這些情感。
楊富閔:
我從小在大家族長大,祖母是我相對親近的一個長輩,以前我每天追著她作殖民地歷史的口述,幫她解超多奇怪的夢,聽她談著我們這一宗族的各種掌故,其實她不愛出門,因為她腳不好,個性也很低調,她只喜歡跟我說,而我也很能聽,很能問。這樣的掏心掏肺,每天我們都在客廳上演真情指數。〈為阿嬤做傻事〉這篇文章長一萬多字,完成速度快到不可思議,這也是唯一一篇,我寫到哭出來的文章。那是二○一三年,書在排版、設計等流程,祖母突然過世,正在守喪,我記得,我的信箱同時出現兩種東西:一個是出版社寄來的電子檔文稿;一個是葬儀社寄給我校對的訃聞。不同的主題,本質上是一樣的事,我對創作的態度突然變得超級嚴肅,不管對於文字、對於祖母,乃至正在寫作中的自己。後來我跟編輯說,留給我一篇大稿的篇幅,大稿有多大呢?那時的責編逸華非常體貼,他說儘管來!儘管來。因為他的打氣,我就安心的關起門來,將《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的最後一篇完成。這也是我很愛的兩本書,許多文章後來被編入很多選本,我開始大量進入校園演講,也是始於這一套《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

許明德:
你的祖母,甚至諸多女性人物:曾祖母、母親,她們在你的作品,扮演相當重要的腳色,特別是祖母跟你說的殖民歷史和宗族掌故。我想你的童年生活,想必對你的寫作有很大影響?可否簡單談談你的文學養成。
楊富閔:
我的文學養成超不文學。大家族的生活,充滿各種儀式性的場面,我的童年因此非常熱鬧:誰家在嫁娶、誰家在謝土、誰家神明聖誕千秋、誰家在煮油飯、誰家在辦喪事,祖母與我,常常「代表」我們家,出席在上述的種種場合,所以聲光影音的感官刺激,比起文字書寫,可能對我的影響更為直接,效果更大。新版《花甲男孩》書封有個文案──從儀式到文字、從說話到寫作、從音聲到風土、從鄉域到想像。可以說是我對文學的一個自白。此外,從小就是電視兒童,那時我的房間,有一台父親尾牙抽中的超小電視,不用跟大人搶。但我看電視有個自覺,就是知道自己想看什麼,一大早會去翻報紙看節目表,把喜歡的通通用螢光筆畫起來,以此規劃我的二十四小時,那些節目:比如介紹台灣山川的行腳踏查、在地小人物的勵志故事,鬼影追追追,台語歌唱大賽,豬哥亮歌聽秀的各種版本。我好像已經在「自主學習」,建構自己的審美,並且學習從台南大內出發,去觸摸世界的邊界,去感知世界離我多遠。
許明德:
難怪我總會在你的作品中看到許多流行曲和電視節目。現在你其實也轉而成為了新興媒體的一部分。從〈暝哪會這呢長〉拿到臺灣文學營創作獎首獎,你在這些年來裏做了許多跨界的嘗試──《花甲男孩》改編成電視劇,《我的媽媽欠栽培》則變成了臺灣新歌劇,文學作品的跨界製作,也讓我們看到富閔作品的多重面貌。我知道你一直希望寫成一個老作家,放眼未來,你希望以後會有怎麼樣的嘗試?
楊富閔:
文學改編或許不是新的題目,古典文學的經典演繹比比皆是,但在當代新興媒體的視野,我們現在理解一個故事的方式,正在劇烈變動。瘋傳、截圖、追劇、人設……這些詞語的運用,也在暗示一種新的識讀模式的誕生,而作用其中的語言文字,正在熱切等待我們將它重新定義。對於一個文學創作者,我感興趣的仍是:文體如何與媒體繼續天雷勾動地火,文字如何展現它的「燒怕電」的特色,跨界是一種破壞,如何在跨界之中,保有一份語言的自覺、文學的清醒,越來越難,但我願意繼續挑戰。《花甲男孩》的各種改編,提醒了我一種故事,怎樣各自表述;《我的媽媽欠栽培》結合傳統國樂,融合美聲歌劇、偶戲,歌仔戲等形式,最後變成一種無法定義的新的發明。其實二○一六年參與 「書店裡的影像詩第二季」,走訪台澎金馬四十家獨立書店的踏查書寫,我就已在慢慢離開學院、回到文學的第一現場,並嘗試結合兩種視角,去探問文學在當代的意義究竟為何。我的跨界之旅是根基在自身的寫作脈絡,可以與我的作品產生連動效應。所以,我要做的,就是繼續努力把自己的作品寫好。

許明德:
談到你的各種嘗試,我知道這一年來,除了在創作以外,你還一直在不同的大學授課。教學的經驗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影響嗎?
楊富閔:
這幾年來穿梭在台灣各地的各級學校,演講場合從國小國中到碩博士班,這些經驗對於我的文學寫作與文學教學是很有助益的,我在到處說故事,認識讀者,同時練習當自己的聽眾。真正進入大學教室開始談授文學,則是讓我的思考變得更加立體,原來只是紙上天馬行空的各種宏大遠景,有了一個具體落實的對象。我發現其實我對於研發「教材教法」的興趣也很濃厚,同時,我想我們可以嘗試重新去問什麼是「教室」。我們都去過「音樂教室」、知道有「舞蹈教室」、「美術教室」,那麼:文學可以有文學教室嗎?我覺得,我與學生就是在拆解、裝潢與重構一間文學的教室。它非常地動態。加上我又很愛寫,所以常常在寫教學日誌,反思每一堂課的班級經營。這些日誌又與我自身的創作,形成一種對話關係,隱隱然朝向一種文論的建構,等於把我既有對於「文學」的認識,推地更深更遠了。
許明德:
最後,我們來談一下未來的規劃吧。
楊富閔:
寫作、研究與教學,猜想是未來我的生活的主場景。就以寫作來說,《賀新郎》作為一個十年的自選,它也在提醒未來十年,乃至更久的時程:怎麼寫?寫什麼?過去十年,我替自己的文字工程鋪下許多基礎建設,加上身心狀態也漸漸成熟穩健了,整個人,比較「深刻」,也比較有肉一點(摀臉)。未來想必不會停止創作,確實手邊已經寫完另外一本新書。繼續開展文學與歷史的對話、不同藝術媒材的跨域連結是一定要的,而我要做的就是深耕心靈的內容,墾拓想像的疆域,讓自己的生活充滿創造力。
|許明德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博士。研究興趣包括元代文學與族群問題、明清戲曲及詩文評論等。曾發表〈西遊:中亞紀行與蒙元帝國的建立〉、〈感舊與奇情:略論豹翁30年代初的兩部世情小說〉、〈明清之際夏允彝之死及相關悼念詩文之敘事策略〉等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