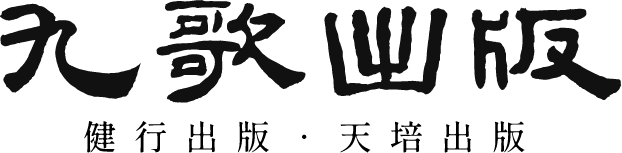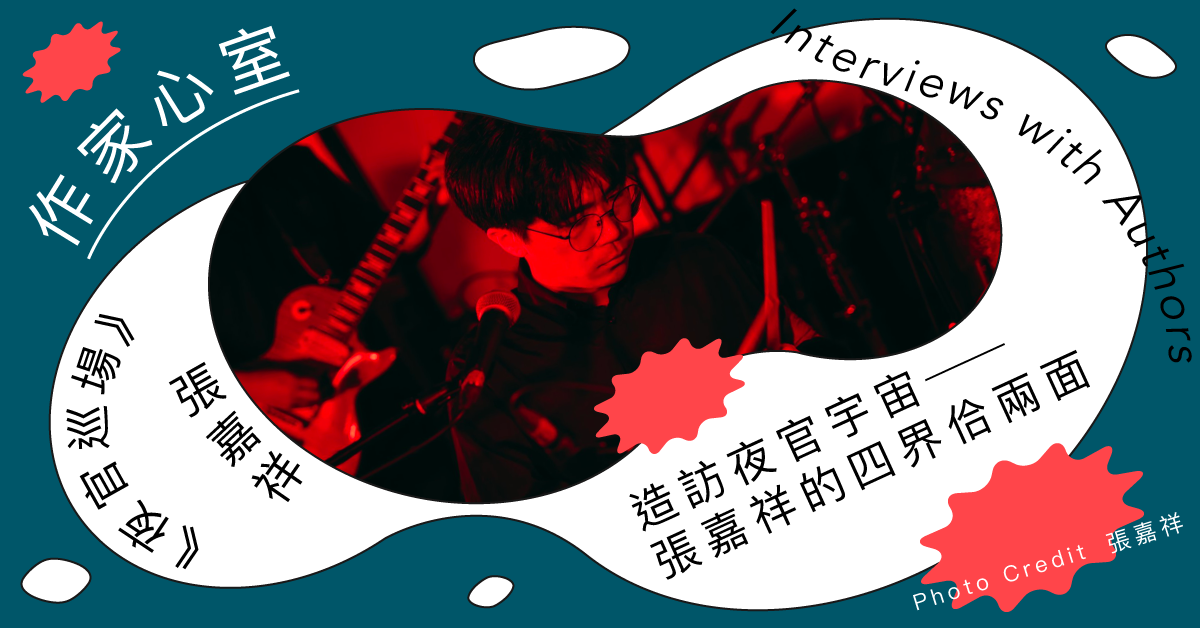記性的衝擊──張亦絢讀《山地話/珊蒂化》
這是一個二十一世紀臺灣文學工作者的身世溫柔揭祕,編織他的元素既有楊牧或巴代等大家,也有唱山地情歌的林玉英;有部落髮廊裡的《中國童話故事》, 也有「很能轉述部落酷兒性」的新一代作者Apyang。在這個我們可以論及「記性的衝擊」的歷程裡,一種「敦化南路的至高性」(或是今天更常會說的「臺北一○一」)可以說──已然,悄悄被掉換。
十二歲時,同班有個同學偷偷告訴我:「我是滿人喔。」
「真的?」我失聲問他:「那你怎麼辦?」
──我們剛讀完「驅逐韃虜」,韃虜就坐在隔壁讀書,好難想像,他有多寂寞。當然還不懂什麼是漢人中心,只隱隱感覺,不知是哪,不太對呀。
這句「那你怎麼辦?」後來變得不只與滿族有關。換成女性、工人的小孩或是同志等諸多被殖民或霸權擱置無視的身分經驗,這問題可一路問下去。幾乎也從「那你怎麼辦?」可以變成「那我們怎麼辦?」──這個「大多數排除的大多數」(見註)問題,不時迴盪我心。教育社會學中或許有一章,女性主義或階級批判的理論應該也有若干概念,然而,我終於看到對這主題最全面、最聰慧、最勇敢,載歌又載舞的美麗迎戰姿態,是在這本散文集《山地話╱珊蒂化》中。

出版過數一數二的詩集《細軟》的馬翊航,有著如含羞草般靈巧的敏感度,如今指的不只是感官,也包括文字與思考向度。他寫酒醉時是「耳裡楓紅層層」,隔著車窗見物「有一種礦物感」,外婆皮膚薄如「乾蒜皮」,某個影像畫面 「光線讓物件有著髮絲般的刺眼邊緣」──這些固然令人讀了,神經會如電到般快 感林立,但還不是最厲害的。有些成分始終都在,比如臺東池上,比如卑南,比如 「還想嫁呢」的娘氣娘腔──然而,整體而言,我認為全書處理得最好的,是我一開始提到的「那你怎麼辦」主題。
〈補修、修補,然後住在自己裡〉是論述性格最鮮明的一篇,裡面有句話表示:「我們能否讓形形色色,取代堂堂正正?」這句漂亮的話,絕不是動聽的口號而已──所以我們會在這篇當中,看到馬翊航如何將平埔多個大異其趣的「還我名字」故事,各自提煉出一句話。因為形形色色的關鍵不只是生理模樣或生(不) 平,關鍵更在記憶的部署:我們多元什麼就多記什麼,而我們想要怎麼多元,也會決定我們怎麼記憶──在其他篇章裡,我們也看到這種身體力行──形形色色,不只是族類,也包括了每個個體,本身的多樣性經歷點名。多元就是:不只要「多元」──還要「多多元」。
〈攤開時節〉寫在高雄媽媽檳榔攤幫忙的兒時經驗,對照被學校簡化的檳榔形象;〈娘娘槍〉模糊軍事戰鬥與美少女戰鬥的界線,不再只讓雄壯的軍旅形象,專美於前──我還很喜歡〈四大天王並沒有來〉與〈姑姑說〉,這些寓論述於童年場景中的書寫,簡直經典。
〈姑姑說〉裡有一節以「陸森寶」為題,短短幾句話,就勾勒出「對話與邀請落空」的反文化交流現象。小孩的大方分享與滿心期盼,以一種天真敞亮的氣氛,令我們在哀而不傷中,瞬間明白了關於大結構的許多事:真像卡夫卡會說的故事。
同樣是一派澄明輕取禁忌的筆法,也在〈教師的鄉村〉與〈走險〉兩篇中看到。前者寫被誣賴,後者是「兩小不是真的無猜」──這兩個事件中,都存在「從不想像小男生會受害受傷」的成見暴力。值得閱讀的不只是戳穿成見──除了心疼,我更對文中如詩的高度結晶化技巧,深深折服。
林玉英/山地情歌合集
這是一個二十一世紀臺灣文學工作者的身世溫柔揭祕,編織他的元素既有楊牧或巴代等大家,也有唱山地情歌的林玉英;有部落髮廊裡的《中國童話故事》, 也有「很能轉述部落酷兒性」的新一代作者Apyang。在臺北讀書工作的馬翊航, 也混有「西部時間」與「東部童年」──八歲父母離婚後,更身處「家人倍增」的 情境。很可能因為這樣的「變動與離合」,令他對記憶有著「錙銖能較」的非凡能力:說到時間,四歲半不等於四歲;敘述空間,不是池上,還有許多招牌名──這種極端的具體化,為讀者創造了一種劇烈的臨場感。在這個我們可以論及「記性的衝擊」的歷程裡,一種「敦化南路的至高性」(或是今天更常會說的「臺北一○一」)可以說──已然,悄悄被掉換。
掉換得真好。
註:轉自孫梓評,〈一時停止〉裡的詩句「我是大多數排除的大多數」,收於即興創作團體「寫信給奈良美智」出版的《雨日的航行》,出版年不詳。
|張亦絢
一九七三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看電影的慾望》,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 /巴黎回憶錄》 (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獲openbook年度好書獎。二〇一九起,在BIOS Monthly撰「麻煩電影一下」專欄。
網站:
nathaliechang.wixsite.com/nathalie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