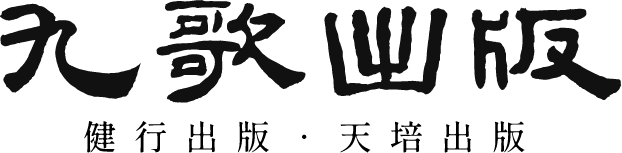褻瀆作為求生:玖芎 X 吳曉樂《我把自己埋進土裡》對談側記
玖芎的第一本散文集《我把自己埋進土裡》(以下簡稱《土裡》)將自我毫無保留地揭露於讀者眼前,以文字記下赤裸殘酷的女性成長物語。新書分享會邀請作家吳曉樂於台中梓書房進行對談,兩人從家庭、創作、性、愛到政治、文化、認同,時而一針見血時而戲謔,召喚彼此經驗記憶中的痛感與共感。
開場玖芎提到寫作《土裡》時,參考不少台灣近幾年出版的相關主題書寫,其中包括曉樂的散文《我偏偏不喜歡》:「能把想法講出來很需要勇氣,社會禁忌源自大家檯面上不想難看,或某些傷害本身就難以啟齒,因而選擇壓抑。」然而前人坦率的書寫,也鼓勵她把這本書寫出來。
▎第一件事,你要有點痟痟的
聊到付梓成書前的幾番波折,玖芎表示沒有出版社願意出她的書,便開始在網路上將散文連載,一篇一篇發,剛開始都沒人理,直到第八篇〈痛覺失調〉,這篇是關於渣男和被騙砲的故事,才引起比較大的迴響。那時當事人揚言提告,曉樂義不容辭相助讓她感念。
於是玖芎問曉樂,是什麼初衷支持她去關心他人、為議題發聲?曉樂笑談──第一件事是要有點痟痟(siáu-siáu),這很重要。「以前的我遇到事情非常壓抑,這跟台灣的教育有關,我們很擅長息事寧人,而通常去『寧』的都是弱勢的人,大人物會有人幫他撫平爭端。當有人說『你不要這麼計較』,這一定是上位者對下位者說的。」她很早便發現社會常見的表面和平遊戲,也不諱言自己小時候非常擅長,因為唯有如此才有辦法活得好一點點。然而一路裝到二十多歲,遇到任何不舒服的事都忍下來,突然間就覺得自己生病了。
曉樂接著提到讀完《土裡》時,跟友人討論的落差,友人擔憂作者的心理,她則認為:「難道大家看不出來作者非常有生命力嗎?沒有生命力是無法支撐她寫完這一切!」她也隨即補充──我們是不是太小看一個人,玖芎跟文字之間已經走到這樣的關係,展現出非常大的意志,各方面都已相當完整。

▎散文通常很靠近虛擬
兩位談及散文和讀者的非虛構默契,很容易被認知成是真實的、是親身經歷,小說很多時候明擺著告訴讀者這是虛擬,但它卻很真實。因此大家常開一個玩笑:「小說通常很靠近真實,但散文通常很靠近虛擬。」書寫親族時,可能筆下的人大都還在世,會發現彼此的認知、回憶裡的對話竟然相差甚遠,甚至出現一方很受傷,一方完全沒有記憶的情況,像是虛擬的。
當出版散文集時,面臨的是另一層壓力──一切不再只是「我」寫下我所看見的,而是所有人都看見。大家是否就認定我是這樣的人?尤其寫到父母時,情形變得更複雜。玖芎認為自己的狀況很微妙,擔任里長的父親是公眾人物,所以之前在故鄉根本不可能講父親壞話,其他人都會說你爸做得很好、很熱心,但事實是父親根本就沒回家。
玖芎說到出版《土裡》後,家裡非常反彈。而她父親則用一種奇妙的方式思考:「他當然喜歡名聲,也明白就社會正向意義來說,作家是有名聲的。所以即使我寫了一本在罵我家很爛的散文,出版後他反而一直在書籍相關的資訊、貼文底下留言,將它視為榮譽。」原本父女兩人的關係就非常疏離,父親反而在散文出版後,開始大聲宣布「那是我女兒,九歌出版了她的散文,以後還可能拍成電影喔。」
玖芎選擇以如此直面的方式書寫,也是因於她的家庭、她的父親,讓她不得不採取貼近現實的寫作策略。她也觀察許多有家庭暴力或對家庭漠不關心的父母,通常都有一個共通性──他們在外面表現很優秀,大家認為非常盡責,表面工夫下很足,可一進家門竟然就翻臉了。很多兒童沒辦法跟他人說自己父母的作為,因為家庭之外的人認知的父母都是形象良好的。

▎無情可以抵抗家庭的招降力
討論到父母對下一代施加的招降力,玖芎認為家庭的招降力會那麼強烈,是因為上一輩保有的的義務感:「對上一代來說,這些都是道德義務,沒有什麼你要不要、我想不想,就是必須這麼做。」中華傳統裡孩子就是必須服從父母,但不討論父母對孩子所施行的正不正確,這是玖芎最不能忍受的。遇到年節,玖芎表示自己有時候會說不,因為她會焦慮到無法踏出房門,家人不能理解她的焦慮,反而對她的「不回家」心生埋怨。
「我發現只要夠無情就可以抵抗家庭的招降力。」玖芎談到家裡很重視傳統道德,從小她就常被罵不孝女,當一個字眼罵了一百遍,它就失效了:「我覺得做不孝女是好的,女生為家庭付出那麼多,每次都被當成局外人。招降力在我身上已經微乎其微,如果真要說有什麼招降力,就是我媽會傷心。」
兩人接著聊到父母跟孩子之間的關係,玖芎覺得當一個人沒有自主權,就不知道人跟人之間其實是有界線的,會衝擊這條界線,於是發生衝突。曉樂則認為可以理解很多時候需要家庭給予無條件的支持或關心,問題是現實並不總是這樣。看《土裡》時,更意識到「家庭就算看似完整,裡面的人還是有可能感覺自己像孤兒」。
▎「洞」的殘酷隱喻
曉樂在閱讀《土裡》時有兩個感觸,第一,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這本書,她會想到「洞」。一方面書中不時寫到,要不斷放東西進來,就好像自己破了一個洞:「惡劣的家庭關係加劇破洞的程度,東西進來也會馬上流掉,認真在裡面好好放東西的人少之又少。」曉樂接著說第二個讓她想到「洞」的理由是:「在男性的心中你好像就是一個『洞』,他們只看到有沒有辦法從你身上得到性的好處,其他時候就跟你的家庭一樣,完全不關心。」
「這件事很殘酷,但高風險家庭出來的孩子,愈有可能被人利用和變成傷痕累累的狀態。」玖芎直言,她最近看到採訪,有些詐騙會鎖定未成年或家庭弱勢少女,因為知道她們缺錢、家庭有問題、學歷低、年輕最好騙,她認為這也是一種社會之『洞』。玖芎進一步談到很多少女會答應是因為真的什麼都沒有,只能拿青春換取,就為脫離現在的處境,可是交易的代價基本上就是不公平的。
她說自己最近在看丹麥女作家托芙的哥本哈根三部曲,一本有關童年、青春與人生的自傳性散文。托芙出身於貧窮家庭,長相平庸,小時候特別羨慕同街道上長得漂亮、受男性吸引的女性,玖芎表示「至少她們可以去換一個逃離原生家庭的機會。但對托芙來講很難,她的生活環境跟文學絕緣,但夢想著當詩人。」不知道該說幸或不幸,托芙遇到的骨董書商,沒有要她以身體來換什麼,只是一直借她書。
曉樂說看《土裡》時常感到人與人相處之艱難。書中寫到跟H君的關係,當時玖芎年紀還很小──「我們很容易愛上假貨,一來真貨難判斷,二來必須承認很多時候假貨也帶給我們很多。」當一個人內心已如此脆弱、寂寞,虛情假意也無妨,就算他所給予的無法久存、副作用很多,在那個當下感受仍是好的,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劃下火柴的瞬間是快樂的,但熄滅了更加孤獨。
▎劃火柴劃到土耳其
到土耳其留學本代表著新希望,留學作為一種社會成就,象徵在他鄉或許將有更好的發展,玖芎卻娓娓道來她的種種幻滅。「土耳其是個非常保守的地方,在這裡你只會看到一堆護家盟。」書中寫到,教授曾在課堂上問她會不會聽廣播節目,她回答會聽,不過裡面全是總統艾爾多安的發言,令她感到無聊,結果因為這件事,課後被叫進辦公室警告不能說執政者的壞話。
她接著分享最近土耳其國內新聞,當地有位女歌手在演唱會上開玩笑,說樂手讀過宗教學校,所以一定有變態的一面,引起政府不滿,土耳其是伊斯蘭教國家,不能容許信仰遭玷汙,女歌手因此被警察以污辱宗教罪名抓走。她認為:「在這麼保守的環境裡,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還談什麼追求知識呢?」曉樂回想自己在台灣唸大學的階段──「那時好像不曉得在幹嘛,但異常歡樂。一樣是讀大學,土耳其比較像在求生。」
講座尾聲,曉樂溫暖地總結道「蔣亞妮講過,有些散文看著看著,到最後你就希望這個人幸福,我在看《土裡》時就是這種心情。看到一個人非常認真做了很多事,現在終於有個安定。」這將不會是句點,而是有待開啟的新篇章。
㊙️ 對談番外篇:
曉樂發現了人在現場的作家謝凱特,也邀請他分享他對《土裡》的讀後感,曉樂也補充(推坑)說明:「談親族書寫一定要問問他,凱特寫過《我的蟻人父親》、《我媽媽做小姐的時陣是文藝少女》,都處理過這個問題。」
凱特先說起自己收到《土裡》時,本想先翻翻看,沒想到隔天就看完。「散文這個文類在大家心中很常跟現實畫上等號,所以我會非常顧慮身邊的人在當下看到時的反應。」凱特認為他跟玖芎在寫作上有個落差,「落差點是我其實一直在思考,要怎麼做一個比較好的降落,讓大家閱讀時,每個人都不會有太強烈的情緒起伏,同時又要賦予它文學意義和目的。」盡心思索兩者平衡也讓凱特花費更多時間修改作品。
而玖芎選擇以不經修飾的方式書寫,讓人有種「如果不這樣寫、不寫出來,可能就難以生存」的直觀感受。凱特提及閱畢散文後,看了張亦絢的導讀,深感認同與佩服:「亦絢曾說過在追求文學性時,有一派像我這種,知道讀者要什麼,把文章經營得像讀者想要的樣子,傾向昇華或追求美文的部分;可有另一種文學性是真實的,而那正是貼近玖芎作品最棒的地方,是無法取代的。」

「就散文而言,真實性非常難傳達。」凱特表示:「但如果有像玖芎一樣的生命力,那就把它寫出來吧!這些東西都是文學。我相信你一定想過這些事,可是知道如果不這樣寫會受不了。」至於散文能不能寫身邊的人?凱特說媽媽看了他的作品,也會到處跟別人講「這是我兒子寫的」,然後不忘補上一句「我其實沒有這樣啦」。對他而言這很正常,甚至反而是最真實的部分,「我們在任何人面前擺出來的都只有其中一面,包括我們最親近的家人或伴侶,所以當我媽說自己不是這樣的人,我可以理解,她沒說錯但也沒有全說對。」
對談整理/林鈺芩、洪沛澤 場地協力/梓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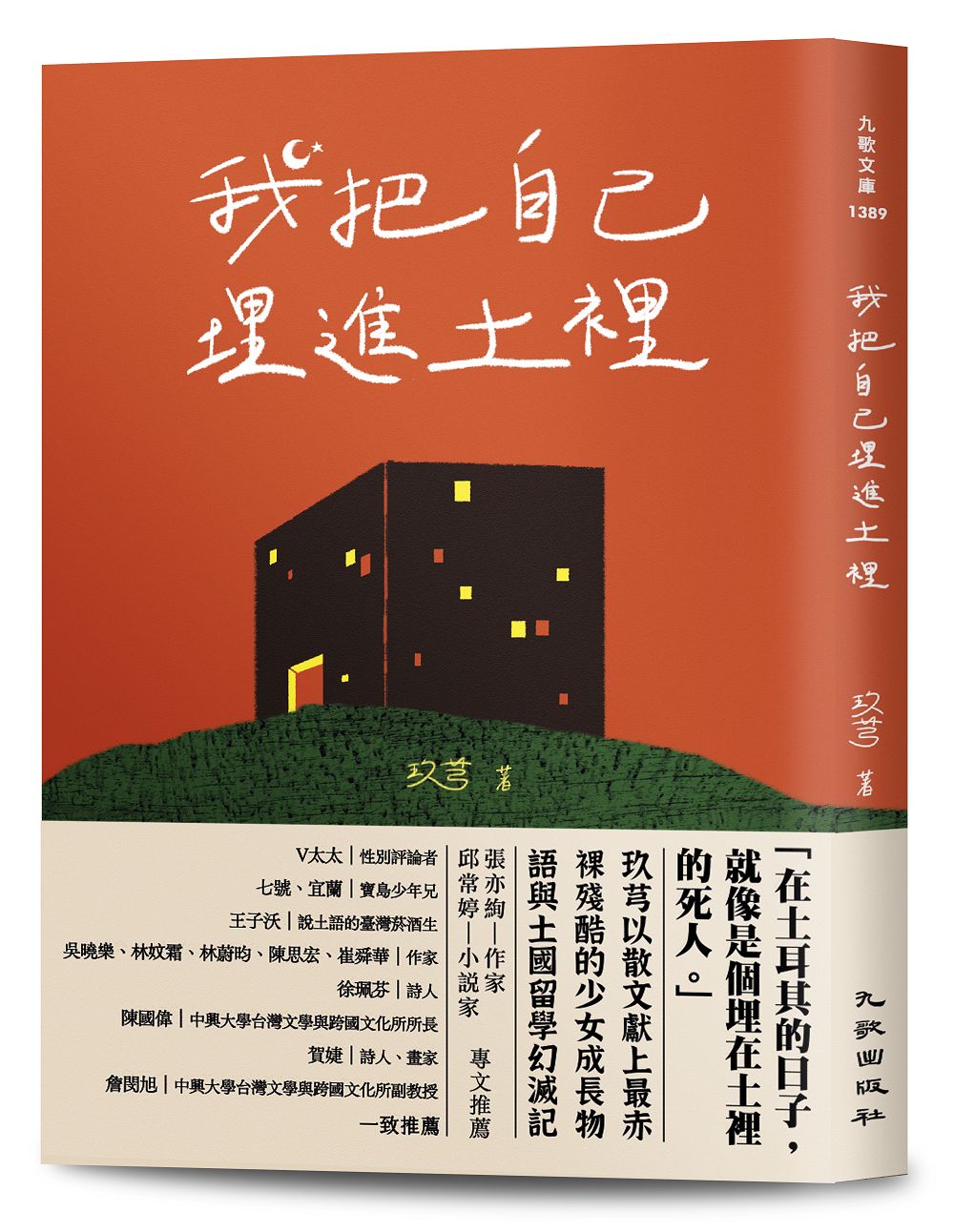
|玖芎
玖芎,Kiú-kiong,1996年出世,宜蘭人,2015年到2020年完成安卡拉大學土耳其語言文學系學士,目前是興大台文所研究生。2019年年尾予台語chim tio̍h, 自此綿死綿爛。佮意動物較贏人類,逐工 lóng leh 練成做兔仔ê魔法。
|吳曉樂
居於台中。喜歡鸚鵡,日夜期待隔壁的小孩成為了不起的音樂家,因為人的忍耐是有極限的。著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上流兒童》,前者已改編成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