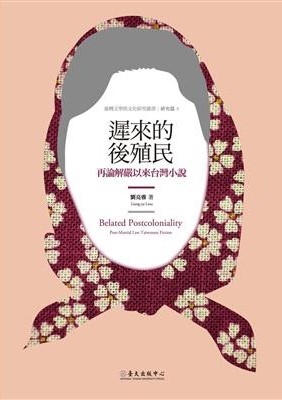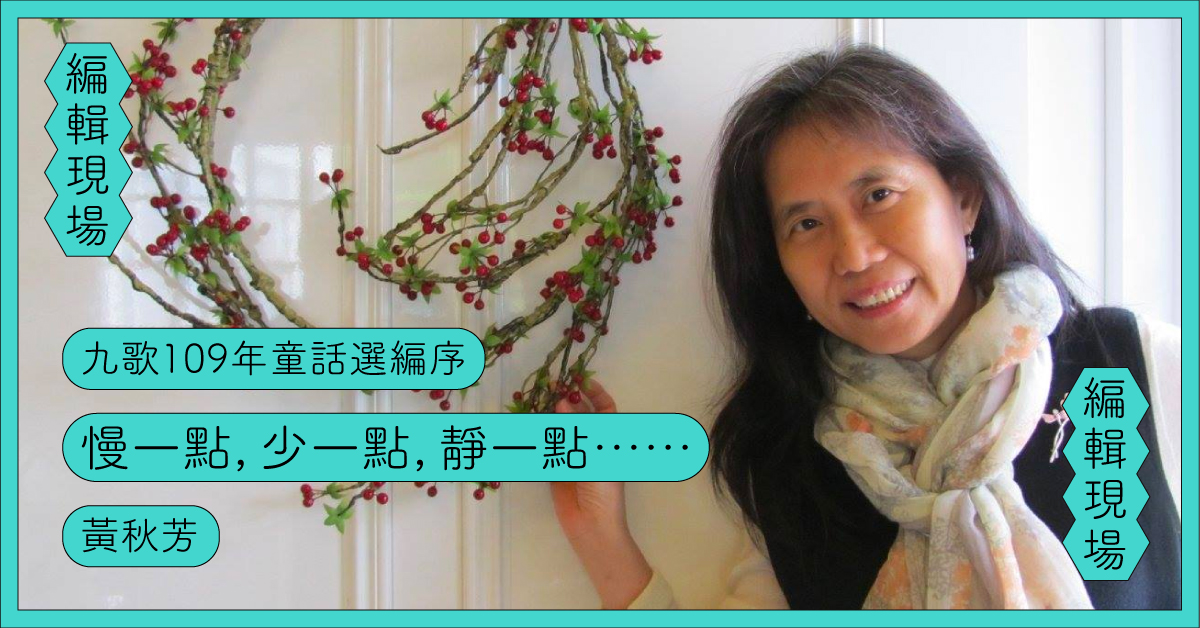解嚴後臺灣囝仔的三合院創作課:劉亮雅、楊富閔對談(下)
由臺灣文學學會與國家圖書館主辦之「2020夏季閱讀講座:集結,千禧世代作家:新世代作家圖像」講座,今年五月下旬於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三樓國際會議廳盛大展開,而本場次〈解嚴後臺灣囝仔的三合院創作課〉即為系列講座之一。主講人為小說家楊富閔、與談人為國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劉亮雅。本場次並於七月四日圓滿落幕。本文即為該場講座精彩的對談紀錄。內容經由主講人楊富閔與劉亮雅教授修訂完成。
劉亮雅:
《花甲男孩》裡許多篇呈現宮廟、乩童文化乃是一種精神傳統,當然它主要是祈求平安、豐收、福氣,但在小說裡此一精神傳統又連結到一些家族問題、親子問題。例如〈有鬼〉裡遭家暴的女子離開夫家跑到臺中設壇,專門幫人處理婚姻家庭問題,最後夫家的女孩找上門來,她起乩答問時,公與私似乎很難分辨。〈神轎上的天〉裡孫女突然看出起乩的阿公砍傷自己是在替砍殺媳婦的兒子贖罪,而懇求阿公停止自責。〈花甲〉裡的父親是因為孤兒身分、缺乏父母關愛而忙於宮廟事務。因此我想要問你,你是否很有意識地想要呈現宮廟、乩童作為精神傳統與家庭創傷、親子創傷有所關聯?你是否還有其他很多與宮廟、乩童文化有關的議題想要處理?
楊富閔:
我會將老師提及的宮廟、乩童文化視為民俗敘事的一個環節,而民俗敘事確實瀰漫在我從第一本書到此時此刻所有的作品之中。對於這個議題,我似乎意猶未盡,探索不盡,它顯然不單單只是一種題目的操練,它必須回到我的生長背景來看。
首先,我是在廟邊長大成人,故鄉的媽祖廟是我們庄頭的大廟,亦是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除了庄頭大廟,臺灣鄉鎮到處可見的宮廟,也是我們生活的主場景之一,換言之,庄頭大廟與地方宮廟彼此之間形成一張綿密的人際網絡,我是在這張網絡裡面長大的。廟邊長大的我,廟務與家務常常綁在一起,我們過的生活是日曆紙上的大字的,也就是國曆,也會是小字的農曆。我祖母形容國曆叫做?个(他們的),農曆叫做咱个(我們的)的。我家歷代都有跳宋江陣的男性長輩,儼然是個家族傳統,自然遇到神明聖誕千秋,動員參與的祭祀活動就會非常的多。我到現在聽到廟會敲敲打打的鑼鼓聲響還是會很開心,聽到遠方正在施放煙火,忍不住會去一探究竟──我很好奇。
民俗活動帶給我的影響非常深遠,它也自然進入我的文字書寫,而落實在不管是《花甲男孩》乃至我的其餘創作,它是埋針一般的進入日常生活的肌理,提供一個我也醉心其中的時間感知系統。換言之,民俗元素或許並非作為啟動一個情節的道具,我在書寫這些民俗敘事,我都在處理時間的問題,這是以後十年我在創作時後漸漸察覺到的。老師講的一點都沒錯,關於民俗敘事的題目,先前我曾提出一個寫作計畫「鬥鬧熱──跨文類民俗敘事創作計畫」,我已經在上半年的防疫期間將它寫完。
換言之,回到一個創作論的問題,為何是民俗敘事呢?我這幾年在研究所的訓練,我不得不去注意到民俗此一題材從戰前到戰後的各種變化,當前也有許多關於此一話題的研究,我覺得它終究要抵達一個方法論的提出,而形成我在《花甲男孩》的文案文字所企盼的「從儀式到文字」的美學關照。
我們看到民俗敘事被放在理性與啟蒙的框架之中,民俗敘事也常常跟鄉土文學一起登場、民俗敘事甚至牽動國族認同、肩負各種任務,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民俗敘事與表音記字的關係,以及其所牽動的關於虛實之間的驚人效果,李渝的〈夜渡〉給我很大的震撼。民俗敘事如何重新定義我們對於「文學」的認識,這裡到處都是繁文縟節、眼前都是飄來飄去的符號,你如何不被約束而舉重若輕呢?以及剛剛提到的時間性的關係,都是這個議題吸引我的地方。花甲時期,我的思考還很平板,我也寫得不夠好,但花甲時期的九篇小說都與民俗敘事有關,我會繼續拓墾這個題材,讓想像的疆域越廣越深。

劉亮雅:
你的「新鄉土」另一個特色是你替許多長輩,尤其女性長輩塑像,例如曾祖母、阿嬤、姨婆,當然還有媽媽,這與九○年代江文瑜提倡書寫阿嬤的故事應該很有關係。你和女性長輩特別親密。你對曾祖母和母親的描寫相當逗趣鮮活,但寫到阿嬤的時候則比較悲情,因為她是丈夫早逝留下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在家族分產上居於弱勢,又因為二爺爺的來到,被大家指指點點幾十年。〈為阿嬤做傻事〉這篇散文幾乎像是祭文,卻是在寫阿嬤與二爺爺不被家人和鄰里接受的關係。有些文章裡說二爺爺騷擾阿嬤,有些則寫二爺爺對阿嬤也不錯。有好幾篇都寫二爺爺對於沒有血緣的你和你哥哥非常好。所以我想問你,為什麼有點叛經離道地揭露家族隱私、呈現阿嬤是個所謂「敗德」的女人?呈現二爺爺時夾雜同情與批評?為什麼呈現的版本也有不同?揭開隱私勢必造成困擾,這會不會阻撓你繼續披露?
楊富閔:
版本的不同,或許顯示我對這些事情本身的看法,隨著年紀與心境的變化,也不太一樣了,時間已經給我答案。下筆過程恐怕不是橫衝直撞的,而是痛苦萬分、反覆斟酌,然而我已越過這些問題帶給我的焦慮,特別是在青春時期。但我珍惜、也重視我所寫下的每字每句。
我的爺爺非常疼愛我,我的小學教育,他也是參與最多的長輩,爺爺給予我的關愛特別強烈,同時讓我明白:那並非理所當然,而這是多麼重要的生命教育。愛是一個很古老的題目嗎?我覺得這個題目正要甦醒。二十一世紀,請問「愛」要怎麼寫?我已離開二○一三年寫作《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那個階段很久了,比較密集處理家族敘事也是在這套書。我更像在廓清一個迷霧,我已經走過那團迷霧,而我的文學觀念告訴我:寫作不會拿來解決問題。寫作就是時間。我跟我的作品往前又走了一段路。
最近出版新書《賀新郎》,是自我的冀許,其實我有死而復生之感,或者生如同死的微妙感受,因為透過自選,我在「喊停」。這才發現還有很多寫作情熱,走完寫作的第一個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都大過寫作,不會為了寫什麼而做什麼,反而是生活引領我遇到這些題目。這也可能是我的作品,也常給人一種很散文的印象。
劉亮雅:
你的「新鄉土」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強調「心靈」。「心靈」比較屬於現代主義,在傳統鄉土小說則很少見。你的「新鄉土」摻雜現代主義,在描寫家族史的同時,也想要讀每個人的心,呈現圓形的人物而非扁平的人物,例如乩童和參與宮廟與心靈創傷或自責有關。你的散文在描寫庶民的同時也是自傳、回憶錄,有許多的自我反省、自我剖析。包括《為阿嬤做傻事》裡有幾篇對於自己是否要立志當作家的舉棋不定,在《我的媽媽欠栽培》裡有一篇對於自己的書寫與記憶是否夠真實的自我批判。對於書寫位置的反省涉及你內在的複雜矛盾,例如你從小就想要離開家鄉、你的鄉土書寫大多是在離開家鄉後所寫的。你被家鄉的鄰居小妹稱為「臺北哥哥」,因此你描述自己的書寫位置是從騎樓下望進屋子裡,「既親且疏,介入又不介入」。因此我想問,你對於傳統的鄉土小說不滿意嗎?你又如何定位自己?你是否覺得一個人要離開家鄉才能夠書寫家鄉?這與你想要呈現鄉土的真實與複雜有關嗎?
楊富閔:
老師的這個題目讓我很感動。我過去十年以來,似乎就是在丈量我與文字的關係,我沒有不滿意當前的鄉土小說,我反而覺得臺灣文學的語言真的非常熱鬧,過去我的閱讀比較雜食,加上雅俗界線比較稀薄,這也讓我留意到了許多看似不夠好可是我覺得非常讚的作品。〈字幕組創作課〉這篇文章因而算是我的文學告白。而如果以《賀新郎》自選集來回到老師提及的定位問題,收在全書的〈大內楊先生十二位〉則是一個自信的答覆。這十二個人物都是自我的裂變──「遠親」,大概就是一個相對理想的位置,我在自己的作品,住成開枝散葉之後的一位遠房親戚,遠親有多遠呢?有時難免也對自己說聲富閔好久不見。換言之,對我來說,書寫故鄉確實需要一個距離,卻非真是物理意義上的近與遠。這時遠親兩字因而給我許多想像空間。

劉亮雅:
在描寫宮廟宋江陣、八家將時,我覺得你的立場曖昧反覆、變化很大。你的父親幫忙宮廟事務,管理宋江陣。但母親似乎反對過於投入,對你哭訴。你也很討厭一位父親身邊的叔叔。你的國小同班同學有好幾位在教室裡表演乩童,甚至拿美工刀割傷自己,你也曾遭到他們霸凌。但你也描寫返鄉在橋上看見八家將打扮的同學醉倒在路邊,他的轎班只剩一班,讓你想起小時候曾與這位同學玩在一起,後來則是負責監督他們的好學生、班長,回想到這裡,你覺得自己內心狂狷,其實和他們很相似。我想問,你對宮廟民俗藝陣的立場為什麼如此曖昧反覆?似乎有一些你還沒有寫到?
楊富閔:
如同我們在第六題提到的,民俗敘事於我來說是一個寫作方法的探究。而我從這些民俗敘事之中,看到自己一路以來的心境變化,看到心靈佈滿香灰,曾經以為寫作能夠將它拂拭,但香灰卻是落滿了手。我是住在這個時間裡面的一個人。
《花甲男孩》到《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對於民俗敘事的看法必較類似,那時我也還在寫作初階,還在膽戰心驚的學習走路,自己要用什麼語言,對於文體的自覺也很薄弱,初來乍到這座城市,還在適應,很沒自信。這也形成老師提到的曖昧反覆的問題,同時也可以回答在處理家族私史的狀況。我對寫作的態度、觀念,乃至於我與寫作共存的方式,漸漸找到平衡之後,希望以後這些曖昧與反覆,或許不再只是一種反映論式的呈現,而更應該朝向一種形式表現的技術。
我覺得2016年出版《書店本事》,實地走訪臺澎金馬四十家獨立書店之後,我的寫作型態已經有了變化,它讓我的身心完全大開;2016年我也協助《花甲男孩》的影視改編,則是完全把我拋入一個不可測的識讀環境。這些都與過去的寫作習慣大不相同,關於「文學」的定義正在逐漸改寫,我不可能不去注意到當前人文環境的劇烈變化,我覺得是天搖地動的。而回到處理民俗敘事的角度,2018年寫完《故事書》之後,許許多多束縛被我放開了,隨著自己的年紀、關懷、乃至理想的堅持,民俗敘事這個題目於我已有不同意義,實與虛的辯證應該有比過往複雜,希望很快修改完成,陸續發表出來。
劉亮雅:
我在一些故事像《花甲男孩》裡的〈聽不到〉和〈花甲〉裡隱隱感覺到同性情慾的流動。我想問你,未來你會想要更直接地處理鄉下酷兒嗎?
楊富閔:
這兩篇小說距離現在已經快十年,回看這本集子,在命名上以男孩定錨,後來細看,原來《花甲男孩》不單只是〈花甲〉那篇的主角,每篇小說都有一個或者多個類似《花甲男孩》這樣的男性人物,這本書我寫了很多位花甲男孩,而老師提到情慾流動的部分,在這本集子之中相當薄弱,我自己也很困惑,為什麼這麼少?現在我在回頭去看,猜想那時我的生活重心、人際關係都還在變動之中。我似乎更著墨在處理家族與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沒有側重在情慾或者身體的探索,愛情也寫得非常少,少到後來改編電視,大家都發現這一點了!記得編劇在影像化的過程中,就有擷取情感此一角度去發揮,所以劇中的愛情線是新增添的,這讓花甲的故事多了新的面目。我不確定以後會直接或者間接處理這個題目,但一定跟過去的想法,很不一樣了。

劉亮雅:
不同於許多新鄉土作家,你的作品以散文居多,只有一本小說集。我猜想,這可能是因為你念研究所,沒有太多時間經營小說。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你比較喜歡寫散文。我看完《為阿嬤做傻事》和《我的媽媽欠栽培》後,再回頭重看《花甲男孩》時發現,《花甲男孩》裡的阿嬤有你的阿嬤的影子,但個性上比你的阿嬤強勢、新潮很多。有些論者認為小說與散文未必能截然劃分,也就是寫散文未必沒有虛構的成分,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你認為寫小說與寫散文有什麼差別?紀實性與虛構性你比較看重哪一個?
楊富閔:
老師說得沒錯,首先,我可能太喜歡寫了,以至於我對於紀錄生活樂此不疲,其實,我也有寫日記的習慣,若以字數來論,我的寫作量真的很驚人。但我對出版還是有個堅持,它必須是個系統性、脈絡式的出版,因而我會非常看重「成書」這件事,而不單單只是「結集」。我的每本書至少在私我的意義上,我覺得它們彼此互為鎖鏈,可以照見自己有沒有進步。
而我覺得告別學生階段之後,我的作品也有會有新的形式出現吧!時間多了未必寫出的會是小說,我最近很想去做Podcast,或者製作文學教材。我覺得當前對於小說散文的區分,它跟文學市場的區分很有關係、也跟文學教育的課程分類密不可分,而我自己覺得我的創作應該大於各種分類。再說這個區分往往還會出現飲食散文、旅行散文、鄉土小說、都市小說等,我一想到心就很累。後來我出的書很像散文,但是我相信只要編輯策略與裝幀方向有些改變,《故事書》、《賀新郎》它也可以長的很像小說。
而老師提及的紀實與虛構,我反而留意到,自己很愛讀日記、書信、傳記,臺灣文學史料在這方面收穫豐富,自我的各種形貌變的非常立體鮮明,這類型的作品讀不少,有些並非除自文人之手,但這更加吸引著我。我現在看網紅拍片,背景常常都是自己的房間、客廳,家人親友都入鏡了。他們家用什麼牌子的衛生紙、看哪一臺的電視,赤裸裸來到你我的眼前──「真實」的形貌如此動態,我不可能不注意到這給文學造成的衝擊。我很喜歡You-Tuber稱呼自己為創作者。我在文學找不到答案的時候,常常在這些還在成形、看似變動中的新媒體生態圈,找到許許多多的慰藉與共感。

劉亮雅:
未來你是否會繼續寫小說?會想要寫那些題材?你曾在〈花甲〉裡嘗試科幻小說,以後會再繼續嗎?
楊富閔:
首先我要再次謝謝劉老師這十二道題目,讓我得以藉此梳理文學的從開始到現在,這些問題我很珍惜。對我來說,這也是2020年一次值得紀念的文學討論。我不確定是否會寫「小說」,但確實在過去幾年的寫作長征之中,不少故事始終沒有寫到,我可能捨不得寫、或者覺得準備不周、時間不夠、語言不對。其實每天花在寫作與閱讀的時間很多,我的寫作是屬於紀律性的,現在每天我都固定寫個一千字,對於要長、要短、要快、要慢,也很清楚自己的習性了。至於要寫什麼題材呢?手上已經完成一本文集,我也才結束一年兼課的工作。我很真切地察覺時間真的有限:時間是公平的,沒有時間,什麼事都做不成。所以現在很懂得把最清醒的時間,留給自己敲敲打打,一定要寫!我有張計畫書,但從不按計畫走,未來希望自己可以過得安靜,生活簡化,相信那時我的文字文體也會有新的變化。
編按:
本場講座劉亮雅教授共計提出十二道細膩深刻、且具延展性的論題,在歷經兩個半小時的對話之後,隨後即與與會的學者、聽眾進行交流。其中,現場聽眾針對楊富閔頗具自傳色彩的兩本著作《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的書寫語言進行分享,聽眾指出「囝」仔與「囡」仔在讀音與用法的差異性,楊富閔也表示深受啟發;其次,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阮斐娜教授,同樣從楊富閔用字策略進行精采的提問。阮教授以楊富閔的作品〈暝哪會這呢長〉為例,指出楊富閔語言的活潑性,其中描述親屬關係「姊接」兩字,在聲音(聽覺)與文字(視覺)形成的特殊聯想。
對此楊富閔則從兩方面加以回應:首先指出,網路語言與文學語言之間的相互滲透,它已改變我們對於創作的體感。楊富閔進一步表示,早年初步接觸殖民地臺灣文學,諸如新文學初期賴和、楊守愚等前輩文人的作品,以及部分的歌仔冊史料。特別能夠感受語言文體的駁雜與彈性,這也對他的閱讀慣習,造成相當大的挑戰。然而楊富閔卻也指出,此時此刻,重讀殖民地時期文白交錯的文字創作,反而正是時候,一如我們當前常在路上,看到各種通過拆解形音義而形成特殊閱讀效果的招牌標語等──正是在摸索文體、尋找讀者,乃至自我定位的創作道路上,台灣的新文學因而有了跨越世紀的連結、對話與啟示。

|楊富閔
1987年生,臺南人,臺大臺文所碩士班畢業,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目前為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臺大中文系、清大中文系與東吳中文系兼任教師。作品計有《花甲男孩》、《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休書─我的臺南戶外寫作生活》、《書店本事:在你心中的那些書店》、《故事書:福地福人居》、《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編選《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與梅家玲、鍾秩維合編)。作品曾獲改編電視、電影、漫畫、歌劇。
|劉亮雅
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碩士,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任臺大外文系特聘教授、臺大臺文所合聘教授。曾擔任2006-2008年臺大外文系主任。主要研究臺灣當代文學與文化、英美二十世紀文學、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理論、同志理論。著有《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2014),《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2006),《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2001),《慾望更衣室:情色小說的政治與美學》(1998),Race,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 Sula, Song of Solomon, and Beloved (2000)。與人合著《臺灣小說史論》(2007);主編、導讀《同志研究》(2010)。曾編譯、導讀《吳爾芙讀本》(1987),導讀、審定《海明威》(1999)、《康拉德》(2000)、《吳爾芙》(2000),導讀《簡愛》(2013)。

《賀新郎:楊富閔自選集》
作者:楊富閔
《賀新郎》選錄楊富閔文學歷程的代表作品十七篇,一方面帶領讀者穿越楊富閔十年以來的文業長廊;與此同時,透過打散重編,全書除了宛如為一則全新的長篇故事,亦彰顯了楊富閔文學的另類視野,也是楊富閔對於「當代」/「文學」的提問與回應。全書一氣呵成,充滿作者對於文體追求、形式摸索,乃至內容生產的繁雜思考,而文學創作的基本單位──語言文字,則是選集收錄的美學準則。《賀新郎:楊富閔自選集》更是一份來自富閔的文學契書,對於文學創作的超前部署,熱情預約臺灣文學的下一個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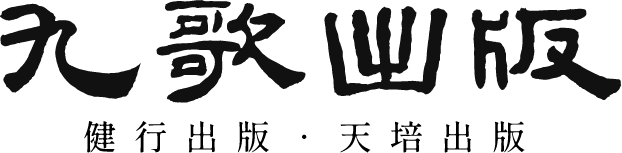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