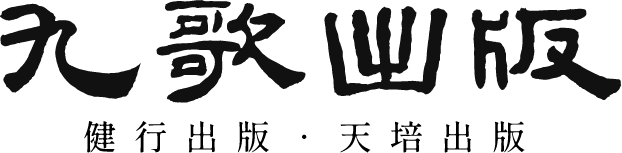這就是厭女,我在寫的過程不斷挖自己身體裡面的刺:劉芷妤導讀《證詞:使女的故事續集》活動側記
當父權結構的問題再度浮上檯面,眾多新聞媒體卻以「雞排妹事件」為題,指向的問題在哪裡?我們清晰看見權力的不對等,卻不一定能找出問題核心的所在,那是潛藏在每個人身體裡的一根刺。2020年《證詞》於台灣出版,本文為同年9月九歌出版社與MR Book Cafe 月讀合辦,邀請作者劉芷妤為讀者導讀的活動側記。
「別以為瑪格麗特・愛特伍筆下的基列共和國,只是小說裡的幻想情節,一不小心,那就會是此時此刻這個厭女世界的前世今生。」──劉芷妤

《使女的故事》是愛特伍在1985年寫下的,但在川普當選後的這幾年,它又突然間被大家討論起來,突然間從一本小說,變成了影集,然後走向街頭。如果要很粗略又不爆雷地說,那麼這個故事的時空背景是距離1985年兩百年後的世界,發現了一些21世紀初的史料。美國境內崛起一群激進的右派團體加宗教激進團體,反抗了現有體制,獨立成為一個基列共和國。那時想像的未來,也就是現在的我們,身處的是一個經濟大蕭條的時代,核廢料影響了大部分人的生育能力,於是禁止所有反自然的節育行為。
這件事滿有趣的是:1985年寫的《使女的故事》,是1985年的瑪格麗特愛特伍,寫了距離現在(21世紀初)兩百年後的世界,發現了我們現在的史料,而作者還說過,這本書寫的都是她寫作之前曾經發生過的事。於是,現在的我們讀這本書,就變成作者跟讀者,未來跟現在、甚至還有過去,以及過去的過去,互相發生一種微妙的互文感,我們在閱讀彼此對「女性」這件事情的看法。
但反烏托邦的小說那麼多,本來,你可能會想,小說家嘛,總是會加油添醋,你不會覺得那是真的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可是川普當選讓這一切變得好像可能發生了。2017、2018年,穿著使女打扮的人大量出現在世界各地,我認為是川普這樣一個行為舉止的人當選世界大國總統這件事,催化了《使女的故事》對我們的威脅感。這些「使女」站在白宮、站在波蘭華沙、站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她們在爭取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婦女生育的選擇權。

對於婦女生育選擇權還要爭取這件事,我之前是無法想像的。回到我們自己的國家來說,我是一直到2018年11月24號,與同志婚姻、性別教育相關的公投結果公布才發現,同溫層外的世界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我一直以為非常平等、至少是「想要平等」的這個國家,做出了與我想像中完全背道而馳的決定,這件事情令我非常震驚。那時我想到《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並不是在講同性戀與其相關的事,它是在講婦女的生育權。但我們用同樣的邏輯來推衍的話,如果11月24號這樣的決定發生了,那麼我不能說《使女的故事》不會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我不能這麼肯定了。
像這樣的說辭我們是熟悉的:「生育率越來越下降,要是讓同性戀結婚、讓女性擁有墮胎的自主權,人口不是會越來越少嗎?」聽起來理由超正確的對不對?在基列國,它的理由更充分,因為那是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而且整個世界一直生出畸形的、夭折的胎兒。
在故事裡他們稱這些畸形的胎兒叫「異嬰」。
在這裡我想特別談一下「異」這個字,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它指的是一個「和我不一樣,所以你就是不好的東西,我必須把你剷除,或至少保持距離」的狀態。比如說異類、異形、異己。而「異」用得最正面的時候在哪裡呢?異性戀。很好笑吧,在所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負面用語之中,異性戀彷彿是非常正常,非常值得成為主流的事情。
而這個「正常」與「主流」,就是基列會被建立起來,並且存活那麼多年的原因。之前我和朱家安對談時,他說過這樣的解釋:因為我們人類需要一個秩序,我們想要知道我們可以把錢交給誰,交給銀行員,因為他穿著制服,我們交給他錢就不會弄丟;交給便利商店的店員,也因為他穿著制服,能替我們換到一些我們想要的東西。可是這個秩序經常是危險的,因為永遠會有例外,你可能覺得偶爾有例外也沒關係,但是有的例外,一旦發生,便經常無法挽回。
我們習慣跟小孩子講說男生要穿藍色,女生適合粉紅色,建立性別分界,也很習慣跟小孩子說「你再不乖的話我會叫警察來抓你喔」,這很容易就可以讓小孩子安靜下來,可是講久了他很可能會反過來相信:「警察要來抓我的時候就是因為我做錯事情。」我們就是從這樣的恐嚇裡面長大的,所以我們現在仍然會認為警察就是一種權威。即使讀了很多書,看到香港、新疆發生的很多很多故事,我們仍然會覺得我不要去跟警察衝突、我們不要去做什麼會被抓走的事情,就連我們在遊行的時候都還要謝謝警察。一個權威假設建立起來,它會造成的毀滅性效果是會很強大的,因為那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不再只是一個警察跟一個平民之間的事情而已。

另一個例子可能是老師。我們叮嚀孩子,在學校就是要尊重老師,老師說什麼就做什麼。聽起來完全沒錯啊,然後呢?我們看到了房思琪。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不是一個人講話特別政治不正確或思想有偏差的問題而已,所以對我來講,比起很明顯就是個騙子的韓國瑜,我更在意的是柯文哲、比起川普我更在意的是彭斯,他們很容易看起來道貌岸然是主流的那一邊,但不知不覺地,甚至在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歧視女性,或者在破壞某些事情的時候,便把這個社會變成了他們想要的樣子,去維護父權秩序。
在這裡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父權秩序並不是男性得利,而是男性女性他們各自很痛苦,但是他們無法諒解彼此痛苦的那樣子的世界。
回到故事本身,基列的階層十分嚴謹,不同身分以不同顏色代表。其中使女是血紅色的,是古代西方代表犧牲的顏色,她們代表了生育。假設主教或有錢有勢人家的夫人無法生育,基列就會分配給他們一個使女,讓使女為他們生小孩。
這個在《使女的故事》裡面自述的使女叫作「奧芙.弗雷德」,英文是「Offred」,意思是說,她是一個「Something of Fred」,屬於弗雷德的一個東西。而這個她所從屬的弗雷德大主教位高權重,擁有很大的勢力。故事中每一個使女都叫作一個「of someone」,「屬於誰的一個使女」。另一個階層是嬤嬤,嬤嬤的責任是教養、訓練使女,告訴她們怎麼跟大主教上床、怎麼樣順從、你只能跟主教上床但不可以跟主教夫人搶男人⋯⋯等等。影集裡的嬤嬤長相有點像是還珠格格裡面的容嬤嬤,而她的角色也是那樣,是一種維持秩序的存在。她確實是卑劣嘴臉一覽無遺的角色。但到了《證詞》,她有另外一個面向。我非常非常喜歡《證詞》就是因為嬤嬤仍然壞,但它告訴你她的心路歷程,為什麼她會變成這樣子的人。
《使女的故事》影集,生產儀式劇照。圖/Daily Mail
畫面中間這位紅色的是使女,右邊是夫人,左邊是脫掉他黑色西裝的主教。
故事裡,使女不能單獨跟主教上床,因為這個制度怕他們會產生感情,怕他們真的淫亂起來。所以他們要求生不出孩子的夫人雙腿間躺著有生育能力的使女,然後看著主教,也就是自己的老公跟另一位女性進行性行為。
這個儀式與《聖經.舊約.創世紀》中一位叫Rachel的女性有關,她因為自己生不出來,所以非常寬宏大量識大體地說我的使女在這裡,你就使用她吧,她生出來的就等於我生出來的。這個故事被基列國用來作為這個儀式的正當性,同時拐著彎強調:我們女性,就是應該這麼的求全。他們沒有考慮到也許問題不在女性的卵子,而是男性的精子,他們拒絕考慮這件事情。只要多換幾個使女試試看,總會生得出來。

右下角這位是莉迪亞嬤嬤,她們的代表顏色是棕色。中間這兩位,一個很痛、正在生小孩的,是後面那位夫人的使女。使女在生的時候夫人用腳夾住她的使女,假裝是她自己生出來的。這是一個儀式,它的荒謬跟不符合現實,以及它符合現實的部分,都那麼強烈,以至於觀看時有加倍的痛感。情感上我們覺得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理智上,世界的局勢又讓我們感覺激進主義相去不遠。

在《使女的故事》譯者的導讀中,她提到瑪格麗特.愛特伍在1986年曾經講過:「要記得,她在這本書中用的所有細節都是在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所以,它並不是科幻小說。」(近未來小說或者末日小說或者反烏托邦小說,通常會被歸類成科幻小說)。它是在想像一個未來的國度沒錯,但它用的都是確實發生過的事。這讓我想起我寫在《女神自助餐》書封上的那句話:「本書情節並非純屬虛構,如有雷同,我很抱歉」。我在自己的書上寫下的女性處境,並不完全是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或我身邊的人身上,但它們都是曾經出現,並且不斷出現的。
所以今天特別想要談的是「厭女」,這是兩本書跟現在我們處境的共通點。
容易造成厭女的因素有哪些呢?其中一件就是只用自己的經驗判斷別人的生活,將自以為好的東西套用在別人身上。

我摘出了這段在《證詞》裡面的句子,因為只用自己的經驗去想像別人的生活,便永遠會落入像這句話這樣的困境。男女不平權這個困境,並不是男性造成的,而是這個社會共同造成的事情。它也不是只造成女性痛苦,它也造成男性痛苦。假如女生想要把男女不平權這件事情完全推到男生身上的話,男女平權是永遠不可能達成的。因為我們自己的身體裡面就具備了「你不乖警察會來抓你」、「你不乖老師會生氣」那一種巨大的架構下造成的東西,我們要有病識感才能醫這個病。
這裡我想講一下另一套我很喜歡的書《哈利波特》,我之所以喜歡這套書,因為整套故事裡,無論佛地魔再怎麼樣想傷害哈利波特與他愛的人、致他於死,他也不曾講過真正會致人於死的咒語。他永遠只說那個很基本然後聽起來很沒用的咒語:去去武器走。我先卸除你的武器,把你的武器丟開之後我們再坐下來談。這很深地影響了我在為人處世時的看法,我認為,站在制高點去指責別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我們並不站在那個被指責的位子上。我是一個女性,我也很難理解男性在他們的那個結構下長大,有多難理解女性的痛苦,所以我不是想要指責他們不理解,不是罵贏了就好,而是我們必須雙方都同意這個結構讓我們都很痛苦,然後才可能真正改變它。
在《證詞》裡面還有一段話讓我覺得很荒謬,它說「我們的起心動念是慈善與關懷,我們將要廢除社會墮落腐敗會造成女性的諸多苦難」。若只看這段話,你們會想像它是從一個什麼樣的人口裡說出來的?我會想像它是從想要推翻基列的人口中說的,但它實際上是基列國的大主教,也就是真正造成女性苦難的那個人說出來的。
這種荒謬難道不是最可怕的部分嗎?從同樣的一個善念出發,卻可能走向完全不一樣的方向。基列國的大主教真心認為:「我們過去和女性承認平等是一件太殘忍的事情,因為以她們的天性來說,平等是不可能的。為了降低她們的期望,我們秉持著慈悲開始採取行動。」他是真心的耶!這種真心不是聽起來很熟悉嗎?不只發生在小說裡,電視跟網路新聞上也常常看到。因此,我也會常常回過頭來問自己,我期待的平等正義是不是在某個我不知道的層面上會迫害誰?
另外一個容易造成厭女困境的因素是,把女生界定為好女生跟壞女生。「當有人對你做了可恥的事,那種恥辱會沾染到你。你會覺得自己被弄髒了。」這是書中一段自白,同理,如果太接近其他女生的恥辱,那種恥辱也會沾染上身。那種恥辱包括什麼呢?可能是一個潔身自愛好女生不會去跟一個到處跟人家上床的女生做朋友吧,人家可能會覺得妳跟她是一樣的喔。或者說,如果這個女生是一個非常激進的女性主義者,那妳是不是應該要跟她離遠一點,不然的話其他男生可能會覺得妳也是一個這麼瘋狂這麼激進的女生,然後就不想跟妳約會、不想跟妳談戀愛、不想跟妳交往結婚囉?這句話在故事裡面跟故事外面,都適用的。社會判定出一些準則去讓女性遵守與自我審查。
我曾經非常喜歡自稱為女漢子。因為有段很長的時間常在媒體上看到,很多漂亮的女藝人都自稱為女漢子,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會說:「沒有啦,我私下就是大喇喇的」、「我私底下,就喜歡穿T恤牛仔褲」、「我喜歡跟男生打成一片」,那個形象看起來很不錯耶,甚至漸漸變成一股風潮。那股風潮讓我也想成為那樣的人,有女性的外表,卻有男性的內在,這不是很完美嗎?
一開始我的確是很想要朝著女漢子那個路線進行的,我很怕被人家認為是一個女性化的人。我抗拒那種被當作女生的時刻,因為我知道,被當作女生的話,可能會有一些麻煩。那些麻煩可能是認為你心機重、小心眼、認為你關心的就是美妝藝人等等,然後很多負面的想像都會加在你身上,最糟的是那些都很難辯駁,因為那種刻板印象一上身,就不可能證明我沒有心機重沒有小心眼啊,要切腹把心挖出來證明嗎。於是我一直把女漢子這三個字貼在我身上,還努力把「我不是你們所想像的那種女生」也貼在身上,但,不是每個女生都跟刻板印象裡一模一樣啊。這件事情我是在寫書的時候才發現的,就算我喜歡化妝品跟漂亮衣服,那就怎麼了嗎?那代表我膚淺又心眼小嗎?會這樣想的那些人才膚淺又心眼小吧。我真的是到了很後來才這樣想。

但另一方面,我關心社會議題,我有正義感,我會站在運動第一線往前衝,那跟我喜歡漂亮衣服完全不衝突,這樣的我難道不能成為女漢子嗎?我穿著粉紅色雪紡紗的身體裡面就沒有那個充滿正義的部分嗎?然後,我忽然之間又覺得:等一下,我充滿正義跟漢子這個東西是不能畫上等號的吧?我會往前衝,不等於我是女漢子吧?憑什麼正義這個部分是漢子的特質啊?當我開始反省,我才突然意識到:不對,我的特質就是我個人的特質,跟我是不是男生、是不是女生沒有關係。你看,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支持男女平權的人,但我身上居然藏著這麼深這麼深的迷思,對我來說它簡直是一根刺,在刺著我自己,逼著我成為一個男生,避免成為女生,逼著我不能去喝草莓牛奶、不能喜歡蝴蝶結、不能穿粉紅色的衣服。我直到現在還是會覺得很生氣,生氣自己曾經想要避開女性的那部分。實際上,要承認自己,很多時候都是很困難的。
然而這個過程雖然辛苦,我卻是希望自己這樣辛苦的,因為那代表我在反省,我知道我自己心裡面還有很多關要走。而每個人的關卡不一樣,我是這個,別的女生可能是其他的,又或者,男性的關卡也可能因為他們各自的社會處境而有不同。
我喜歡講我自己的關卡,我想讓大家知道寫出這種書的女生也曾經,或者正在,遭受自己心裡厭女的折磨。每次講座,我出門前挑衣服,你們知道我是怎麼挑的嗎?「這件是雪紡,太軟了不行。如果我要穿這件的話我下半身就要搭配破洞牛仔褲才行。」不瞞各位說,即使是今天我都覺得說:「如果今天我要講的是性別平權的東西的話,最好不要穿著太『女性』。」
連逗點總編輯跟我邀稿時,他說:「你來寫一本關於女性經驗的書嘛。」我第一個反應就是:「不要勒。」我很避免去寫女性的東西,原因沒有別的,就是我是一個女生。女生寫女生的東西,很容易被人家說你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上嚷嚷。我不要。我可以寫很大格局的東西啊,我可以寫奇幻,我可以創造一個世界啊。總編輯可能就覺得你在發什麼神經,只是要你寫一本書而已。
後來我察覺到,我這就是厭女。然後我就說好,我們來寫。寫的過程我不斷在挖自己身體裡面的刺,我不知道瑪格麗特‧愛特伍在寫這兩本書的時候是不是。

光是在一個人身上,它就會有很多很多的面向,更何況女性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你如果要用一個「珍貴的花朵」去框架地球上的一半人口,那是做不到的。大多數人都用簡單的詞語去定義什麼是好女人,如果做不到就是母豬。基列國的嬤嬤告訴女孩,因為妳有生育能力所以妳是珍貴的,會被好好愛惜,因此妳不需要反叛。但這個邏輯有許多漏洞:即使妳沒有生育能力,也該被好好愛惜吧?運用這樣的話術,他們告訴女孩不要反叛;而沒有反叛的花朵,也許正是因為都被他們剔除了,並不是不存在。
而厭女困境的另一個面向是罪惡感。基列國的女孩自小擔心,是不是因為自己的腳踝露出來,才「害」人無法控制住自己?這是基列國女孩身體裡的社會的結構,那我們存在的社會結構又是什麼呢?這是我們在思考社會進步、平權的時候應該去考慮的。

這是一個位高權重的嬤嬤所說的話。這位嬤嬤原是美國境內的女法官,在基列國誕生後她成為控制女性的嬤嬤之一。她先是被抓起來、丟進感謝箱。(類似牢房,裡頭沒有其他東西,只有很髒的可以上廁所的空間)基列將她關在裡頭很長一段時間,讓她覺得自己像是畜生,然後讓她住到一個飯店的房間,提供床、棉被、洗髮精等等。然後她說了這段話。當你被剝奪這些很基礎的東西時,你才會意識到自己對這些東西的需要比原先所想像得更甚。現實世界中往往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控制一個女性,並且利用她去控制其他女性,手段就是讓她發現原本的生活是你恩賜的。
然而當人們發現了自己結構上問題,也會如此思考:如果連「警察會來抓你」都不能說,那要怎麼教育下一代甚至是自己?我怎麼重整結構?當原本所相信的秩序已經不再值得相信,會不會全部被摧毀?「當土生土長的基列國少女要去參與推翻基列國的計畫時,她說她很害怕。」我也是,我信仰文學、平等、正義……但是當這些都被某些人用得很俗濫的時候,還要相信這些東西嗎?自己說的東西和他們是一樣的嗎?我會不會也是用得很俗濫的那種人?我不想跟他們一樣啊。
接著我就看到了以下的這段話,這段話我非常喜歡:
「噁並不會改變這個世界,必須弄髒雙手才會。」這句話我在寫這本書和這幾年參與社會運動時感同身受。如果站在旁邊看,你會覺得政客很噁心、政治很骯髒,但站在旁邊覺得他們很噁心並不會改變這個世界,你必須跳下去打他們,跟他們說我覺得這個不對。你要去把自己弄髒、把自己弄得一塌糊塗,這世界才有辦法改變一點。社運的現場,指的不一定是運動最前線,更多時候是從解釋自己的內在蘊含的結構開始。

「能夠閱讀和寫作,不代表就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反而會帶出其他問題,接著又引來更多問題。」出現在《證詞》最後的這兩句話,道出我寫小說和閱讀這兩本書的心聲。基列國的女性通常不被允許寫作,因為這兩件事會讓人「不乖」,但當基列國的少女學會閱讀寫作,她以為自己可以獲得更多知識,但最後卻獲得更多問題。寫書也是,我得到了更多問題,並且無法真正有力量解決它們。愛特伍的這兩本書,會帶來的也許不是外在的改變而是內在的風暴,但只要夠多人的內在捲起風暴,世界就會變得更好一點吧。
《使女的故事》裡面「我」只有一個,但《證詞》的主角有三個,交錯敘事。一個是在加拿大的少女;一個是在基列國裡面土生土長的少女,還有一個是基列國的嬤嬤。《證詞》講的,是這三人如何合力推翻基列國。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至少故事裡是如此。
我真的非常感謝愛特伍寫出這部續集,因為《使女的故事》最後是一個開放性的結局,你不知道這個使女她到底逃出去了沒有。然而《證詞》讓我們知道這樣一個國度是可以被推翻的,它給了我們一些希望。


本活動舉辦於2020/09/05(六),MR Book Cafe 月讀。
書咖歷史不會重複,但必有相似之處——當代經典讀書會:劉芷妤導讀瑪格麗特愛特伍《證詞》+《使女的故事》
|原著: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加拿大最傑出的小說家、詩人,同時也寫短篇故事、評論、劇本以及創作兒童文學。已發表五十多部作品,翻譯超過三十五種語言,其中小說《盲眼刺客》獲頒布克獎,《雙面葛蕾斯》獲頒加拿大季勒文學獎、蒙德羅文學獎。曾因對世界文學與思想的傑出貢獻,獲頒愛丁堡圖書節啟蒙獎、西班牙艾斯杜里亞斯親王文學獎。二○一七年,《使女的故事》改編為電視影集,再度掀起世界注目。愛特伍長期關注環境和生態保育、創作言論自由受政治迫害等社會議題,也曾和全球五百位作家連署,抵制國家對網路使用的過當管制,作品中的「使女」裝扮更成為各項社會運動的符號,如反墮胎法案等抗爭。二○一九年,再度以《使女的故事》續集《證詞》獲得布克獎。
|講者:劉芷妤
無糖,半透明,婚戒戴在食指,肩上有鳥常駐。曾經想要成為精靈但最後失敗了,中年危機是無法世故又不夠純真。
東華大學創英所畢業,寫過幾本奇幻小說,曾經熱愛寫故事也相信自己能寫,但後來被摧毀了,視《女神自助餐》為復健之作,將長期關注的性別議題,以八篇小說故事描繪出不只八種當代女性處境,抵抗成為「那種」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