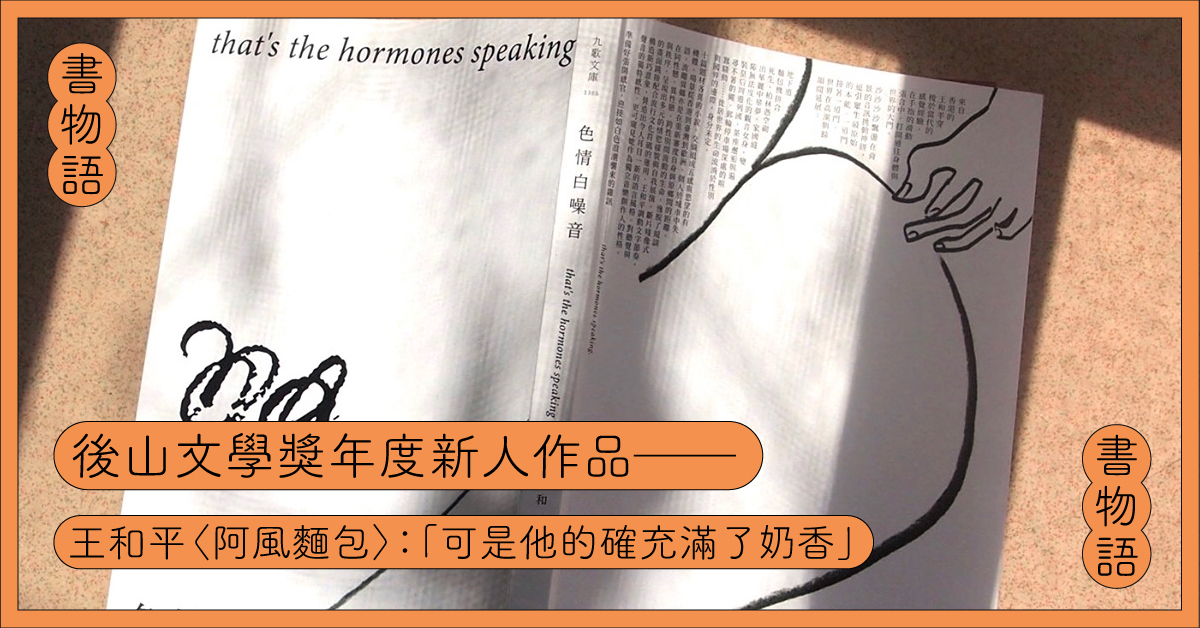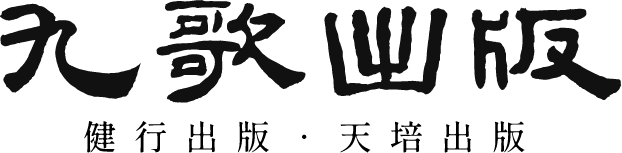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櫻》是一篇一年前就應該完成且出版的小說,最初啟動的心理時間是1998年,然後決定要長篇化的時間歷程是2018年底,接著2019年中開始動筆,結果開始書寫還不到一年就遇到疫情……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因為疫情的關係,身為特殊兒家長,面對未知病毒只能不定期停課,也無法托人帶小孩,無法預料各種時間消耗等等,只得把很多事情都先拖著,所以一路到今天才要出版。
很奇妙的,當初決定要寫這篇小說時,我寫了一篇很長的計畫書,內心充滿著激情與感動,總覺得自己要把時代故事寫下來。這真的需要熱情,畢竟是寫二十幾萬字的故事,又要面對成堆的書籍,來判斷自己到底有沒有寫對的這種歷史查閱功夫,一切都只是最初的情感驅動,「我想把這個故事寫下來」的念頭。
但是不知怎麼,疫情實在很消磨人的精神,且身為特殊兒家長時間就更少了,任何事情都一直卡住,書寫的歷程時間愈拉愈長,作品終於完成時,我竟然產生一種莫名的不安感,我心底反覆自我推測,這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冒牌者症候群」——這種大時代作品怎麼會是我來寫啊……我怎麼有這個資格……(不知道之後《阿香》要出的時候,會不會再一次。)
不知道近日的柬埔寨新聞,會讓大家產生了什麼樣的感覺,對於那些「被騙去」的男女們,不知道大家抱持著什麼想法?
因為新聞很喧鬧,所以我簡單的問了身邊的朋友們,還在網路上海巡看各種留言意見,畢竟這些去柬埔寨的人們,屏除掉刻意去從事非法行業的男女,肯定還有一個數量的人,真的是被騙、脅迫、旅遊而被綁架帶去柬埔寨的。
但我不知怎麼,儘管有這麼多無辜之人,但我發現最大量的意見還是「她們自己笨」、「因為天真不知道社會險惡,活該被騙」……等等之類的意見。
其實我當初看到柬埔寨新聞時,內心產生一股詭異的感覺,只因為這樣的情境,真的非常、非常相似於七十年前的事啊……我這幾年因為寫這篇小說《櫻》,所以一直反覆閱讀「慰安婦」有關的各種文獻,每次看到各種訪談的文獻,當年女子們若能活到戰後,都會生出強大自責「那時候我被騙活該」、「是我自己天真。」、「相信政府」……
明明我們回頭看,其實這根本不是當年這些女子的錯,因為當時日本軍政府因為戰爭需要而去鼓勵誘騙、詐欺、綁架、抽籤等等,將女子送去前線當慰安婦,所以不管如何,就算某個女子僥倖逃開了,也會有另一個女子被騙去,總會有一個數量的女子被遭受此待遇,除非源頭這件事就不存在。
而對這些女子而言,因為這事實在太難堪,所以必須隱瞞一生,因為社會氛圍上,女子們會被責怪不檢點,所以不敢訴說,明明犯錯的並不是她們,但當初社會的氣氛,讓她們必須隱藏起來,直到年老之時,也只有一部份之人願意公開自己不堪的遭遇。
這情境太相似了,所以我看著新聞,忍不住又想起自己正在校稿的這篇小說《櫻》……
每一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的養成背景,不同的背景創造出不同的風格與類型。而這篇長篇小說《櫻》對我自己來說,來自於24年前的一念之間,其實我怎麼也無法想到,1998年的想法,會在24年後成為一本出版的小說,如今回想,實在太不可思議。
24年前,那一年我十八歲,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剪報,大意是這樣「韓國慰安婦……在台灣……遇到神風特攻隊員……」,大意就是一個韓國慰安婦阿嬤來台灣懷念從前……除此之外,當年的我對報導內容幾乎一無所知。畢竟對我這樣聯考時代長大的人,大家都知道「台灣歷史」在當年歷史考試教育中,其實根本不太存在。正因為不存在,所以我當然中文看得懂,但不能深刻理解這新聞背後在說什麼,我唯一能理解到的,就是從報導中得到一種惆悵又傷心的感覺——
很久以後我也才明白,寫故事的時候,先不要管事件背景什麼的,大概也就是要有這種「感覺」,才能夠發展下去。
從這剪報之前話說從頭,十七歲那年,我和同學們不能再住宿舍,大意應該是室友和當時的宿舍管理員處不好,所以被管理員說「下學期不給你們住了」,因為是室友所以被當成同夥,連我也打包一起處理。我心想,反正我家就在桃園,讀的又是桃園的學校,住宿也是學校半強迫的,不用住了豈不剛剛好,便和媽媽說我要買一台捷安特彎把腳踏車,通勤來回差不多六點五公里遠的學校,就此不搭公車了。
依然記得當年這台捷安特是四千五百元之類的價錢,現在不可能有這種價錢了……當年的我因為擁有一台彎把捷安特,開始享有在桃園市區騎車移動的自由,也因為擁有這個自由,最後卯起來和高職同學一起去看二輪戲院電影。高職三年級的六日,我整整看了一整年的二輪電影。
比方星期六看桃園大廟後的金園戲院,明明是夏天但是要穿長褲抵抗冷氣,背包內再加帶一件外套,在金園樓下再買個潤餅,就這麼上樓去準備看個兩部片。星期六看完這金園戲院兩部片,星期日的時候不知道該做什麼,就打開報紙看電影時刻表,再跑去中壢的二輪戲院看電影。(去中壢的哪間二輪戲院我倒是忘了,應該在車站附近吧,不是中源戲院。)
多年後疫情因素,二輪戲院都快沒了,回想起來自己這些二輪戲院的過往,真是往事如夢。
國中開始,因緣際會我開始討厭閱讀教科書,開始熱愛漫畫,所以模擬考成績從高中第一志願一路直直落到公立高職,不過這不是漫畫的錯,單純是覺得反覆考卷的生活很無聊,內心自問自答,難道以後人生所有做的事情,都能夠用「反覆考卷」的模式來做嗎,難道往後的人生,都有辦法預先抽一張考卷來考三回,人生真的能這樣嗎?
其實這種青春期的大哉問,大部分的人都會發生吧(?),也不可能在家族裡面得到解答,問起當時的班級老師,老師們多是師範畢業之後直接來當老師,其實人生經驗很有限,也沒有在輔導學生課業之外的問題,更不可能回答這大哉問,便在我的聯絡簿寫上「Don’t think too much」。
回頭看這段時間,就是必經的人生提問,我身為一個普通人,不在這年紀問自己這問題,就會在後來的人生問。只不過那時代,沒有在輔導小孩心理和職涯想法等等的事,小孩能升學就好,如此的自我叩問從來都沒有獲得解答,最多就是國中美術老師叫我讀復興美工這樣的一句話,總之,帶著反抗的心理,所以課業的內在趨動力下降,這時候唯一讓我覺得有趣的事情,就是漫畫。
考完了一天十張考卷之後,考到答案我都能直接背出來的程度,內心產生很多自我懷疑,由於漫畫出租店就在公車站的後方,公車尖峰時間沒座位可以坐回家,所以我每天就去看兩三本漫畫,等人群散去再搭公車。在一天無趣的考試之後,來到當時代滿座的漫畫出租店,看一本漫畫是五塊錢,彷彿抽獎一樣從櫃子上抽出兩本亂看,總會有機會抽到好故事,讓我短暫投入其中。
在大量閱讀日本漫畫後,很難不喜歡上當時的日本漫畫,並且突然生出一個念頭——「我想當漫畫家」。
這念頭在那時代並非奇怪的事,後來遇到好多朋友在當時都抱持這念頭,那正是台灣漫畫市場的黃金時期啊,各種漫畫比賽開始出現,奇妙的是,當時哥哥朋友的表姐,畫出一篇漫畫拿到了東立的新人賞,知道這件事,對當時的我來說真是巨大的刺激,彷彿我有個路徑,循著軌跡下去也能達到。
儘管事情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但我因為有了個目標,所以我三不五時就去漫畫店,把所有能看的漫畫教學都看了一遍,開始練習各種畫法、消失點、建築物、網點……只不過我畫技始終很爛,大概就是模仿七龍珠、灌籃高手這樣的過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不知道怎樣訓練才是真正正確的方法,也沒有像那些真正有畫技者畫上整天。就像學音樂者要練習六小時以上的樂器,體育專長者全天練習體能,那畫漫畫要怎麼畫才正確,我當時不知道,也只是在考卷畫啊畫的,看不出什麼潛力,如今回想投入其實很少,所以當時的我,其實大概就是把漫畫當成一種「未來」的想像出口吧。
但必須說,那時候的「瞎看」,逐漸累積出一個數量的閱讀量,補足了一部份的心靈養分。除了下課亂看漫畫,放假時就搭公車去桃園文化中心的四樓圖書館的漫畫櫃繼續瞎看,只記得《火鳥》、《怪醫黑傑克》、《帶子狼》,蔡志忠的一部分漫畫作品都是在桃園文化中心看的,反正看了很多,就是沒有在讀教科書,考試都靠本能……
除了圖書館之外,人生中最初始的大量閱讀影像,就在當時的二輪電影院內。
有了捷安特彎把腳踏車之後,我獲得行動自由,在那一年我每週都去看兩部片以上,如此看一年的數量,對一個青少年來說,這已經算很可觀的閱讀量,可以視為時間一年份的影展吧……更何況我很幸運,1997-1998年的電影有非常多好看的片。當時桃園的二輪戲院的特色就是,上映模式是好萊屋電影上映到飽,除此之外看不見什麼歐洲片或藝術片,當時我也極少看到國片,甚至我的李安三部曲是十幾年後才在戲院連續看數位修復版,填補我的時空缺口。
當年的電影正因為特效能力有限,不像現在砰砰轟轟可以特效一直轟,所以大部分故事的真實感很強烈,在那樣的時空中,我在金園戲院看了《搶救雷恩大兵》、《紅色警戒》、《美麗人生》,我每次和朋友說一件特殊之事,那便是《美麗人生》在桃園可是先上二輪,後來因為得了奧斯卡獎大紅大紫,所以在桃園才成為院線片,非常奇特。
這經歷說起來彷彿夢境,更何況當年除了這三部之外,還有《楚門的世界》、《中央車站》等等,真是讓我在二輪戲院受到強大的知識震撼。其實一個年度會留下的經典片不會太多,而這一年對我來說真是精彩。
當年這三部片《搶救雷恩大兵》、《紅色警戒》、《美麗人生》,明明是歐戰與亞洲島嶼的二次世界大戰故事,其實距離台灣有段距離,卻意外啟發了我對台灣歷史的想法,只因為在這一年間看完這三部片後,我回到家打開第四台電視,突然對腳下的台灣故事產生一些好奇,既然這三部片都是二戰故事,台灣又不是沒經歷過二戰,為什麼沒有什麼故事跳出來,讓我們知道?
當然也不是沒有這時代的故事,只是當時的我並非影視、故事或文學的科班生,只是個普通青少年,不容易接觸各種資訊,電視台大部分都在播出港片、好萊烏片,在資訊不豐的情況下,所以就沒看見多少台灣故事,這就是當時一個普通青少年的知識極限。
總之意外的,這三部片讓我啟發了對台灣歷史的好奇,逐漸成為台灣史控,再接連附加二戰軍武宅(甚至有一長段時間,玩的遊戲都是二戰歷史故事),這些知識面讓我往後的故事創作之中,有了一塊很不同的樣貌,影響到了現在。
當年的我還有創作夢想,而漫畫教學的刊物可及性比電影教學的更易懂,所以我把各種漫畫教學的刊物看了好多遍,所以我的故事啟發反而不是「如何寫電影劇本」。當年我從漫畫教學得到最基本的創作知識,就是要「剪報」和「紀錄夢境」,在往後的二十年中,這兩件事情基本上就奠定我的哏庫基礎。
(漫畫對我影響很大,大到好比我想到櫻的劇情時,其實腦中出現的畫面,竟然是是谷口治郎)
回到前面,既然我因為電影的啟發,開始對台灣的歷史故事產生很大的好奇,又因為漫畫教學的「剪報」和「紀錄夢境」,而驅動著我每天看著報紙,好奇有什麼事情發生。
當年代沒有如今方便的網路,所以紙本報紙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某一天翻開報紙,看到這則與慰安婦有關的剪報之後,腦袋陷入極大的困惑,這篇報紙到底在說什麼,我真的看不懂,為什麼「韓國阿嬤……要回來台灣回憶過往」,既然那是痛苦的回憶,那回來台灣幹嘛?
太多問號在我心底,不過就如前面提到的,其實還不知道真實也沒關係,只要有感覺就好了,當時的我還是青少年,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但我看了這剪報之後感覺到主角的傷心,這樣就足夠了。我便把剪報剪下來,貼在大本的空白紙本上,只是隨著升學去宜蘭,我就把這剪報忘記了。考上二專去到宜蘭讀書後,由於我開始學習底片攝影,騎著腳踏車與摩托車在宜蘭四處走闖,在沒有雪隧的時代,宜蘭有著很多剛開始開放的,如設治館這樣的古蹟,我總是有空就去那些地方,整個人融入過往的場景之中。
回想起來我的運氣很好,在一開始的學院系統內得不到的「對生命產生熱情」,最後在環境中得到了。
後來後來,我開始嘗試轉科考試,艱辛的轉來轉去、考來考去,先去台南又去了板橋,最後終於用光獎學金、獎金和打工薪水讀完四年的「藝術創作碩士」,讀的學分是六十個。我終於圓夢讀了藝術創作的學位,開始真正理解「創作」是複雜又辛苦的事,我心底想,以我的性格大概賺不了什麼錢吧。
因緣際會,等成功嶺入伍的空檔,我去拍了《不老騎士》,擔任攝影的職位。
拍紀錄片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追蹤報導」類型的記錄片時間花費漫長,而主要時間集中在一個活動的紀錄片,如《不老騎士》,工作人員則是要跟著老先生、老太太們一起移動,當大家睡覺我們要開會,大家開始騎車我們就起來拍攝,跑來跑去,基本上沒有任何時間休息,真的極度疲累到不行。
不過這過程中也挺有意思的,2007年在拍攝的過程中,原本陌生的老先生老太太們的生命史逐漸出現交集,有趣的是,對這些打過對日抗戰、國共戰爭的老兵,以及當時身在台灣的台灣籍日本軍人來說,在二戰結束六十二年後,他們一起騎摩托車在台灣環島,還真是化敵為友,人生造化難以預料,這是當年怎麼也想不到的人生交集啊。
同時間才知道,其中環島的台灣阿公之一,是當年在柬埔寨訓練神風特攻隊的尉級軍官,他和其他的台灣阿公們一起唱起日本時代的軍歌,對於比阿公們小五十歲的我來說,這一切都彷彿歷史場景跳出眼前。
由於讀碩班時,我開始學習寫起小說,蒐集世界戰爭片與書刊,當時代沒有什麼小說創作課可以上,只能靠著不斷寫來摸索學習,當時我的小說技法不佳,是用編劇大綱的邏輯去寫,只是一個裝故事的殼而已,但至少對故事的想法,已開始逐步建立起來。
在我有了一些敘事技術,且不斷補足各種知識面之後,我開始想寫各種我原本無法寫的故事。此時過往人生中經歷過的事,一個個在大腦中跳出來。
《不老騎士》時的經歷就是如此,我記得一個情境,當時我和另一個工作夥伴在走廊聊天(夥伴的名字我雄雄忘記,他就是寫《不老騎士》片尾主題曲的作者喔,才華滿滿!)在不老騎士拍攝中,由於我看著老先生們唱起軍歌時,我腦中突然跳出了1998的那則剪報,雖然我早已忘記剪報內容,但我記得「神風特攻隊」這關鍵字。
這些年來,我因為成為二戰史控,從大量閱讀中逐漸補足了太平洋戰爭的資料,也逐漸理解了台灣歷史的轉折,這些年過去,我也當然知道慰安婦是什麼了,各種知識補足之後,在拍攝不老騎士時,我腦中突然浮現了一個我想像的畫面,是一個被關在窄窄的榻榻米的木屋中(榻榻米屋就是從宜蘭的「設治館」而來的印象了),一個慰安婦與年輕的神風特攻隊員相知相惜的故事。
我當時對攝影夥伴說出了這段故事,我依稀記得好像是在會議中時,我們工作人員站在走廊上等待,就在這個空檔,我對著同事從頭到尾把故事說一遍(但我想他一定忘了),我在這一刻說出的故事,就是這篇《櫻》的原型,幾乎沒有大的更動,主線就是如此。
這故事讓我念念不忘,總覺得一定要有人把這個故事寫下來,所以當我對著工作人員說出這故事時,我第一次產生一種「題目來找我」的奇特感覺……彷彿是有一個訊號突然接通了我的大腦……
當然我也沒想到,隨著往後閱讀更多文獻與史料,我才發現原來我最初的想像竟沒有錯誤,現實果真比小說更極限,比方前面提到的近日柬埔寨新聞,那種女子們被欺騙、誘拐、或幾乎綁架的行為,在幾十年前其實也就是如此啊。我用這個想法投射過去,完全可以想像女子們心底的無奈與悲愴,光是能存活下來就很不容易。
我對當時的工作夥伴說出這段故事後,腦中就惦記著這故事,一直想寫下來。畢竟且先拋掉沉重的議題,光是以戲劇故事的角度,這些女子內心的狀態,就會是一種「心理奇觀」,我們看見的戲劇,除了無事小說之類的創作路線之外,常見的故事基本上就在描述奇觀……若沒有「心理奇觀」就要有「視覺奇觀」,當然能同時有兩者最好。這個「奇觀」的想法,是我成為編劇之後才開始明確遵循的技法思考,只是2007年的我,並非是以「奇觀」當前提,而是一種創作直覺。當然我也無法說明白,為什麼我會有這種直覺……
所以我總有一種錯覺,那就是我是「被選擇」的,不是我「想寫」的。
接著很意外的,我在替代役時期去了太魯閣,那是一個我腳踏車環島時經過,卻沒有進去看的地方。太魯閣是一個充滿台灣史蹟的地方,從遠古時代到大航海淘金時代、清治、日治時代都很有意思。猶記得我被專車接駁到太魯閣後,就收到一套各種太魯閣的專書,我二話不說很快就讀完,太魯閣的史蹟實在是很精采。
由於太魯閣白天的遊客散去後,晚上的管理處基本上一片暗,我們住在有欄杆圍起來的宿舍內哪裡也不能去,當然原始自然處,其實入夜哪裡也不能去。那情境很有意思,遠遠會聽見水流聲和猴子打架,身在這種充滿歷史與原始生物的地方,而且哪裡都不能去,既然晚上有兩小時可用,對當時的我來說,那當然是用來寫小說。
去太魯閣的一年三個月,讓我思考我的往後人生,在我什麼創作工具都沒有的狀態下,那當然是先寫故事再說。當時的我帶了一台老筆電去,在一個戶外木條桌上,以走廊的燈泡光開始打字。當時的我重新檢查我想寫什麼,理所當然回想起這篇《櫻》的故事。
畢竟剪報早已找不到,當時的網路沒有加入資料庫,什麼也搜尋不到,我也不能去圖書館看微縮膠捲,因為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天。我在想,既然我腦中已經有整個故事,我便採用完全虛構的方法,重新創造一個韓國女子「盧英珠」的經歷。
當年盧英珠被騙來台灣從事慰安婦,而後被管理者毆打而屈服,離家背景,又回不了韓國而憂傷,在慰安所內本要自殺的盧英珠,因為遇見到來的年輕飛官佐佐木而產生情愫。
佐佐木是個家中因牽連政治而家道中落的年輕飛行員,但他投入飛行學校是不得不為(此處的人格背景,我隱隱參考一些老前輩飛行員的背景,當年因為沒有家長與支援,就只能加入軍隊求生,此外也可參考澎湖山東學生事件。)
在盧英珠與佐佐木遇見之後,因為佐佐木心底有個「因為家人被迫害」而生的原則,所以從未與盧英珠「營業」,此舉反而讓盧英珠印象深刻,兩人因而有著更交心的相處,也成為彼此在這時空下互助,小小的空間內,兩人的相處成為縫隙的光。但隨著戰局,台灣不斷被空襲,佐佐木因為被指定要去特攻,在特攻前決定逃去的佐佐木想和盧英珠一同逃走,兩人卻因為誤會而沒有逃開……
兩人錯過彼此數十年後,盧英珠回去韓國之後也從此隱藏自身身份,直到當初在慰安所擔任清潔人員的少年小林才重新連繫上盧英珠,兩人在台灣見面,去看了當年慰安所殘留的遺址,重新將當年的遺物交還給了盧英珠……
當然故事不只如此,畢竟有各種不同背景的女子們,便有著難以言喻的當時代各種心事,女子們彼此支援、互助,終於撐到戰爭結束,回家去後,等著她們的又是另外一場磨難……
大意如此的時代故事,化身成為明確的短篇故事後,我寫完就拿去參賽。當時取名還很困擾,不知叫什麼好,就想著以故事中那棵樹命名,當時的小說就叫做《殘夢之櫻》,很意外的得了當年的南瀛小說獎的首獎。看評審意見之後,其實我有點意外,雖然我的技法還不佳,但評審說「很像電影」。我因為學習電影,所以很像電影是很正常的(我寫的小說有時候也很像漫畫)。
我只是吃驚於,當時的我擔心技法不好,不會被接受,其實是我多慮了,這故事還是能被讀懂。
《櫻》這題目初次被列印成文字後,我收到了作品集,很有趣的,是我當時的替代役室友是韓文系畢業,某天從書櫃上拿了作品集來看,他竟然看哭了,讓我有點吃驚。那天他便順手幫我翻譯的主角的名字「盧英珠」的韓文名字,2008年的我只懂日文,還看不懂韓文字(我要等到2011年才開始學習韓文字),當時同梯幫我翻譯的盧英珠三個字,始終留在電腦檔案內,直到多年後直接納入小說之中。
退役後我決定給自己一段時間,全職寫作到三十六歲,原因很簡單,李安三十六歲才拍第一部片,在那之前以《喜宴》和《推手》得到優良電影劇本獎。(所以三十六歲是沒道理的事,我只是參考偶像人生的時間安排。)
當時的我觀察我的影視同學,大家都受劇本所苦,那我的目標很簡單,既然我以後還想拍片,我必須要有一段完整的劇本累積期,而且必須超大量累積,才不會在真正執行拍攝的時候,浪費寶貴的時間。而且過去數年,我發現我雖然能寫,但能力其實不足夠,必須要像體育班或音樂班那樣的密集且長時間的養成,我才能確定自己擁有這個能力,至少轉換類型的時候要寫得出來。
心中抱持這個「我要訓練」的念頭,我整天在麥當勞寫稿,能發表的文學獎、報紙、雜誌,能寫的全都要寫看看。其實新詩小說散文童話報導,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一樣的,都是乘載故事的文體,我也開始接影視劇本案,但就是沒寫長篇小說,只因為我有點膽怯於自己的能力不足,還不到寫長篇小說的時機,我心底想,四十歲的時候再來寫吧。
而後的我一路發展練習,或許是思考正確,累積哏庫、修正技法,我才正式的開始獲獎累積(所以我確定,之前真的是靠某種天份吧!),但我還是沒有動筆寫長篇小說,只因為我認為累積十年後,我就自然能寫長篇了。更沒想到2015年,不斷長跑的我,竟然因為照顧小孩太疲憊而生病,有接近一年不能寫東西。
在完全失去寫作能力之前,我不敢相信自己會有這樣的一日,打開電腦只想關起來,頭痛、眼睛刺痛,手指會顫抖……原來之前能對著鍵盤一直打字,竟是一種「恩賜」,要同時符合各種條件才能寫,沒有失去過的我當然不能明白,這才知道原來「創作時間」竟是思考力上最高品質的時間,年輕時的自己只覺得理所當然……
而後歷經一年多的各種復健,身心緩緩回復後,時間來到2016年年底左右,我逐漸能以每天三百字左右復健回來,讓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創作之路。
這場大病影響了往後好幾年,也讓我重新思索,自己這條寫作之路能維持到什麼時候,以及我該堅持些什麼,全職工作的前幾年我都在寫劇本或做幕後,每年刻意給自己幾個月,就只寫小說投稿文學獎或雜誌、報紙發表等等,但是因為失去寫作能力一年後,所有進度歸零。此時必然會因此思考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創作」這件事情並非想要就能作,真要因緣具足狀態下,條件符合才能作,而我既然不是永遠擁有這能力,那我必需要在再次失去這能力之前,把想寫的東西寫下來,才不會後悔。
也就是如此,我本來心底預計想要在四十歲才動筆寫的長篇小說,就在三十六歲的夏天開始摸索起來。第一次嘗試的長篇小說是《Rio Douro》(當時參賽要取中文名字,所以叫做《黃金之河》),是講立霧溪淘金史的故事,依然記得我對著朋友在IKEA的餐廳,把這個小說從頭到尾說一遍,雖然第一次嘗試的長篇小說寫的不好,但意外的入圍「台灣歷史小說獎」,如此即可。
在這個獎項的活動之中,我得到許多養分,便把經驗拿來寫助產士小說《阿香》,有了《阿香》的經驗後,便拿來寫樟腦開發的原民淺山鬥爭《血樟腦》,這三個故事陸續得到台灣的長篇獎項,不過因為還有很多細節要校正補入小說內,我會在補足後想辦法陸續出版……
而我給自己的目標,是希望自己能寫到十本長篇,如此也不愧於這些年的學習,有留下東西。
總之,來到2018年底時我便思索,將《櫻》寫成長篇小說的時間來了。既然要寫,就要進行設定的探索。要將一個八千字小說,完整的變成長篇小說(最後是二十七萬字),那多出來的東西,到底要說些什麼才好看,至此必須要決定方向。方向就是,要做完整人物連結,或是全虛構。
在這時刻,我因為重新接觸到許多編劇理論、比方甚至有以AI計算角色份量的這種專書,讓我重新思索各種角色鋪陳的可能性。我決定要以女主角作為主要視點來推進故事,也因為編劇經驗,很直覺的採用全虛構不連結現實人物的寫法,這是我過去習慣的創作方法,對我來說依靠背景而全虛構,反而是更有發揮空間的寫法。
再來是戲劇長度的問題,畢竟我有戲劇編劇的背景,平常要寫個十集電視劇完全不成問題,只是既然要拉長,我採用的便是長篇戲劇的邏輯,人物先拉到三環,接著把時間線畫完,單篇探討主題確定,一環一環的結構累積上去後再開始書寫。(所以接下來要去大學課堂分享,實在可以在這邊大書特書分享經驗。)
而我回想《櫻》的故事,其實我最初有點懷疑該用什麼角色來當切入點,因為主角是個韓國女子,又不是台灣人……不過這個想法很快就消失,因為只要發生在台灣,這就是我們自己的故事,會有「說中文的主角才是主角」,是一種經驗不足時的思考誤區。
既然要寫,當然要做研究,所以大量的找論文來看。(這是我的習慣,讀論文類的文章,然後從參考資料找資料最實在了,我衷心感謝所有研究者。)
儘管我已經閱讀了許多資料,但其實不夠,而且一路讀下來,發現隨著時間,顯然韓國比我們更在乎這段歷史,至少在電影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最特別就是十分催淚的《花漾奶奶秀英文》(I Can Speak),這倒是讓我有點驚訝,因為這故事在中點之前,竟然包裝了一半的喜劇,在戲劇背後所承載的知識普及上,高度技巧的讓觀眾產生情感起伏而傳遞議題,是韓國電影中有關慰安婦議題的電影中,觀眾成績最好的一部。
2019年中開始起步之後,面對龐大的內容,必然經歷很長一段時間的打底書寫,而在這段書寫時間,過程中大概分為幾個奇妙的歷程。
最特別的是,我竟然產生一種從未體驗過的「畏縮期」,只因為我寫到慰安婦的心理面和人身狀態,就不得不描寫到「性」,這是題材必然的過程,就如同寫「酒店」、「軍中樂園」這樣的題材,作者不可能迴避性的內容。這當然是最初就要面對的議題,只是在短篇的時候,我技巧性的迴避掉性的描寫,長篇的時候當然無法迴避了。
一直以來,我有點排斥在小說中去寫性的描寫,更何況對角色女子來說,這些經歷可不是初次戀愛「純純的摸索」或「兩情相悅」,這過程對女子來說是非常痛苦的過程,我在初次打底的時候,愈寫愈覺得這實在太痛苦,寫了許久之後產生退縮之感。
過往不寫「性」的理由很簡單,若是在影視中,出現這種鏡頭很抓眼,但我總覺得,我都還沒有寫出戲劇上最動人的部份,不想要把這張牌用出來,所以非常迴避。如果一個故事中,根本沒有這些「刺激」的部份,卻依然讓人鼓動著想看完,不是很厲害嗎?
當然這只是我的偏好,以前的我是這樣認為,直到終於寫下去之後,這種防備心理逐漸冒起,總覺得這故事如果是女生來寫,是不是就能迴避掉這種感覺?
不過,我依然記得曾經看過一部紀錄片,台灣翻譯成《童心未泯:湯米溫格爾》,講述著名的插畫家湯米溫格爾,同時也是一個情色插畫家,對他來說,兒童插畫與情色插畫是一體兩面的事。不能因為自己畫兒童,就假裝「性」不存在這樣。這部片十分有意思,有許多創作的思辯,不過當事情來到自己身上時,仍會有些邏輯打架。
不能迴避這部份的心理描寫,後來我的克服方法,是要更理解這樣女子的遭遇,閱讀更多這類女子心理的報導,明白各種為難和不得不之後,再加上更多資料的閱讀產生同理。其實台灣的831軍中樂園當然也是相似的議題,戰後的日本也有同樣的議題,愈讀愈多之後心底篤定了,至此,我才終於跨過這個心理門檻。
沒想到,小說寫著寫著,我又陷入一個心底困難,雖然這個困難早就該在2008年時解決,但拖到了2019才開始面對……
我在小說中設定,讓主角盧英珠產生情愫的飛行員佐佐木,正因為不和女主角發生關係,所以才讓盧英珠印象深刻。
我寫小說、劇本的工作邏輯是這樣(每個人方法不同),我會先確定主題故事,鋪完主要情節之後,我才會去田調,只因為先閱讀很多資料,腦中的模糊無邊的想像會很快被收束起來。而我逐漸收束想像後,開始思考,在那樣充滿戰爭壓力,女子幾乎被當作物品的情況下,真會有這樣行為的男子嗎?
我內心自問自答,我是個普通人,如果我屈於壓力,我做得到故事中男主角的行為嗎?
就在內心開始產生巨大疑慮時,因為就讀博班,電影系的吳秀菁老師請我們一起去台藝大的戲院看她拍攝的《蘆葦之歌》,由於我都在看十幾年前的紙本資料,在當時《蘆葦之歌》反而是最近的影視資料,我都還沒去看,沒想到就「送到眼前」……
依稀記得在紀錄片中,有一個軍人「立花」正是如我小說中主角一樣,每次到來只和女子們說話。當時的我看著台藝大電影院的大螢幕愣住了,這不就是我現在腦袋稍微卡關的想法嗎。
在這之後,我又找最前面的日本報導文學翻閱,找到了其他佐證後,內心就篤定,在這樣的情境下,仍有人性之光。
那天課堂之中,我舉手和秀菁老師說出自己在寫的故事中,正好在此卡關,沒想到竟然在課堂上解決的疑慮,如果說這是巧合,也未免太……過於巧合。
彷彿又回到當年2007年的思考,彷彿自己要寫這題目,是「被選擇」,不是我去「追尋」。
另外關於這篇小說中,也描寫了一部分的「神風特攻隊」,由於這已經是台灣好幾個世代的歷史了,大概也被遺忘了。簡單說,台灣島上遍佈機場,而戰爭到後期,從台灣本島的機場派出許多戰機去尋找美軍自殺突襲。其實在小說中描寫飛行是一個困難之處,我想既然有一個角色是個飛行員,如果因為小說技能不足而不去描寫飛行,會是劇情的弱處,繼然要寫,就要來寫看看幾乎被忘掉的台灣歷史,那便是「台灣空戰」。
1944年的十月,這場台灣上空的戰鬥,基本上就是一面倒的毀滅型戰鬥,台灣的機場能量都被壓制與殲滅,往後再沒有能起飛抵抗的能量,也就是如此才會有後續的台北大轟炸,以及驅動上層去採用特攻。
有趣的是,我一直找不到適合的模擬資料,最後竟是靠著《戰爭雷霆》這遊戲去模擬故事中的飛行……其實同時間的學習也用在《徹夜飛行》(今年的優良劇本,希望這故事有好成績),這是我第一次用電玩來達到「情境取材」……
補足了各種需要的資料後,終於一路寫下來,完成了這個作品。總覺得寫過這篇之後,好像其他的故事有一點寫不出來了……
因為疫情,這兩年多我們真的不斷夾縫中求生存,我們住在桃園,因為機場在桃園,所以當初疫情一來桃園就開始緊張,後來小孩班上同學染疫停課,各種問題……我們幾乎都在照顧小孩,而且小孩特殊無法外援,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北孫南送這種事,相信這是類似家長的困境,疫情停課陪小孩一多,東西就沒時間寫,進度不斷往後延遲,已經到了失去控制,只好不斷追趕到趕上為止,真是異常疲累啊,這是我第一次在書寫上,初次產生被疫情影響的不安感。
還好,透過這些文字紀錄,我現在的心情慢慢穩定下來,真心感謝所有幫助過的家人、朋友、國藝會,九歌、慈憶、欣純,各個單位機關與老師教授們,到了這年紀明白一件事情,看似是自己的短暫成功,其實也是環境的支持。
最後回到自己,我想我完成了一個有意義的小說,沒有愧對這二十幾年的時光,希望自己不要再冒牌者症候群了。
張英珉《櫻》
|張英珉
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藝術碩士(MFA),台灣藝術大學影音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博士候選人。曾入圍金鐘獎、金鼎獎、九歌年度小說選,獲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長篇小說作品曾獲鍾肇政文學獎、台灣歷史小說獎、星雲文學獎。
《櫻》榮獲國藝會長篇小說發表專案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