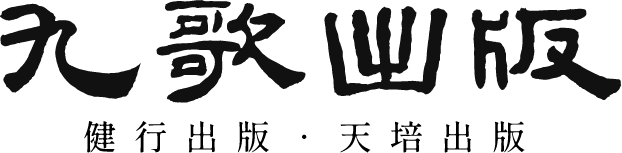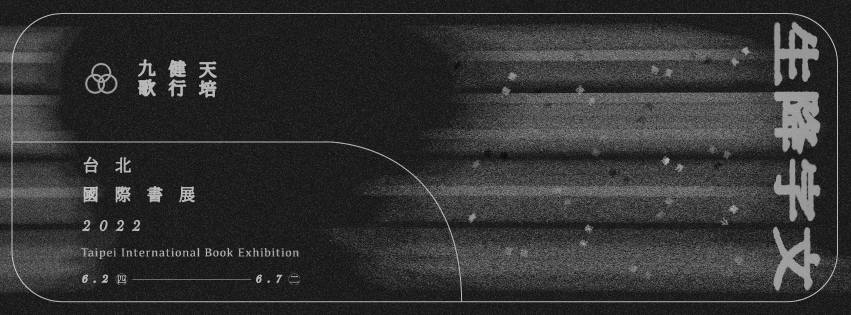講情話給世界聽:馬翊航《山地話/珊蒂化》集序

精準無華的文字,敘述迷離少年之所遇,讀著讀著,有時也讓我驚頓或迷離起來。
──周志文
「你看見的是記憶。你知道那些星星可以有多遠嗎?」
「我才不信,有人摸了星星還不被燙到。如果他能舉起他的手指說,只是被記憶燙到啦!我就相信。」《紅的自傳》裡,Geryon和心愛的男孩Herakles正在看一張照片。Geryon是一隻紅色的怪獸。
《山地話/珊蒂化》也是一部成長小傳。照片裡,男孩歪倒成美人魚姿勢,彆扭且大膽。馬翊航將標籤(原住民陰柔男同志)穿成裝飾,這些「是其所不是」的故事,多半苦中作樂,邊笑邊被眼淚鼻涕嗆到。《細軟》那樣好的文字有了幽默感,怎能不燙。
──陳柏煜
馬翊航英文名應該叫安娜,後面加貝爾就成鬼話,寫錯作BEER變燒酒話。這本書裡都有了,並講成情話給世界聽。
他應該叫羅琳,非常會羅列。散文裡最重要是名詞,排比之間,琳琅大觀,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上林賦,大塊大塊風景,合則寫生,分有靈光,散文藏詩/私貨,少女情懷總是濕。
他應該被尊稱伊莉莎白,慾望師奶偏托生小農村,把產業大道走成紐約第五街,村姑原來是女王,靜如處子,動有觸手,蛋糕上的草莓其實是台灣文學桂冠上的一顆天珠。
他應該叫芭芭拉Barbara,雞毛燥,內容像降乩,文字成佈道,熨斗把一切起毛都壓平,讀完它,世界講話只是吧啦吧啦blahblah,眾皆寂靜,只有他還在吹喇叭,一鳴驚人。
他也可以叫蘿絲。開篇很醉,讀了很醒,自有一道靈光,文學鎖螺絲,幫你上發條。
他是電他是光他是唯一的山地話。四百年後葡萄牙人來到新寶島,以為他叫Dawn潼恩,其實是我們讀了忍不住喊Damn,該死的好。
我僅知道世界上最有名的松鼠叫珊蒂,住在深海的大鳳梨旁,海綿寶寶需要珊蒂,我們需要珊蒂化,透過玻璃罩或是夢幻泡泡,是水還能被看透,世界越是搖晃,越是澄清了。
──陳栢青
讀馬翊航這本散文,時常讓我有著跨上他記憶馬背,跟著一起出航的錯覺,聽他畫外音夾敘夾議訴說著成長風景,在島的東邊,在成為原住民的途中,多識蟲魚鳥獸,也探勘情感關係的形狀,那些藏在蒙古包、錄影帶、四大天王、漢聲小百科縫隙的故事,讓人看著看著回想起那些久未想起的碎片,並且透過這本書漸漸拼起來了。
──黃崇凱
反覆看了三次小馬的新書《山地話/珊蒂化》,第一次用平板讀,最喜歡小馬寫的〈攤開時節〉;第二次用電腦讀,讀全書理路架構,覺得五個分輯鮮明,都能獨立而出;第三次稿子看到一半,結果先在評審現場遇見小馬,我就懂了這本書提醒了我,是它適合各種不那麼乖的讀法。所以我想聽小馬說書,這本書其實是小馬的Podcast,值得我們去思考書面語與口說語之間的種種奧義。
──楊富閔
我們都叫馬翊航小馬,小馬的小大概是種老練的靈動,就連散文也像細細的刺,針灸一樣沒打算讓人見血,可讀了會改變你的筋骨肌理。小馬是池上的男孩,是台北的美少女,是學術世界的模範生,也是酒後的瘋婆子;小馬可以把自己從傷口中反覆接生出來,也可以透過熟齡的世故,將所有幻痛解壓縮,成為深夜酒醉狂歡之後,一次次拓印在濱海公路上的歸途。小馬的散文是沒有要治癒的治癒,是釀過的恐懼,是每個人反覆回家的夜行車程。
──葉佳怡
「讀《山地話/珊蒂化》像是走入隧道,遠處回憶發出來的光,亮晃晃地令人嚮往,但怎麼前進也抵達不了盡頭出口,因為那是已過去的時間。馬翊航的散文便是在不斷回返的步伐間,細緻地向我們呈現回憶之光在牆上的投影。它們是如此清晰可見,仿若就在眼前,令人心生悸動,卻始終有種無法觸及的寂寞惆悵。」
──鍾旻瑞
看馬翊航在《山地話/珊蒂化》裡動員時間,從池上的焚風與霧裡,陰柔男孩慢慢撥開乾草堆,豎起羽毛飛過縱谷,飛到城市,沿途尋找心上人,終於在敦化南路的小公寓裡安居。可安居也是扮演,他總在移動,扮演停留。在高雄生母的檳榔攤扮生意人的孩子卻像個臨演。在繼母的閩南家庭裡扮多出來的乖孫口音卻露了餡。在中年轉行務農的父親田邊迷路,演知路的返鄉青年。又在波士頓北京男人的懷抱裡,被異國化裝了一回寶嘉康蒂。馬翊航在哪裡都像訪客,但過境得像定居,他甚至在愛裡裝病。最終,風吹過,霧散開,馬翊航的散文也就像他曾目睹,踮腳尖走圍牆如鋼索的少女。我貪看他在不安穩的記憶邊界鬆動字詞的形狀、聲音與意義,他的語言是在數字鍵盤之外的*與#,我們曖昧撥打,感覺清純,也感覺色情。只是偶爾,娘娘槍發射,從乾草堆走出的男孩,亦是拒絕在成年禮上扮演阿美族男人的卑南族珊蒂。還有偶爾,成為台北人之後,仍舊把自己活成田野,酒醉睡在東區黑板樹根下,被警察扶起,撥撥頭髮上的土,抖抖翅膀,我很好,華美飛進池上的霧裡。
馬翊航在《山地話/珊蒂化》槍口對準自己,但碎裂的彈片,就這麼卡進了我們心底。
──顏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