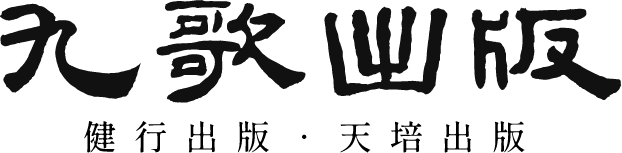像一篇小說那樣看──黃崇凱主編《九歌112年小說選》序
小說是奇怪的東西。小說似乎自由到可以敘述一切,同時也受到各種因素限制。當你看一篇小說,你明確知道這是某人以文字寫就。小說文本通常有個穩定的敘事角度(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有時第二人稱),敘述某些事情。
小說會教你怎麼看。你沿著敘述的指引,經過某些名字、事物和動作,約略能知道發生什麼事,也能從出場的角色、情節,推測這是篇怎樣的小說。你看得愈多,愈能識別不同小說的質地。
篇幅意味著容量。如果是一個短篇,你大約無法期待角色、情節和事件源源不絕登場。因為讀者的注意力有限,也因為作者必須在有限篇幅布置一種主從秩序,組織所有文句字詞,呈現一些特定時空場景下的角色行動、想法和感受。
作品是作者意志的顯影。如果把小說視為建制,我們會察覺作者在文本內部的綿密掌控,換句話說,作者是隱而不顯的獨裁者。
小說渴望呈現,渴望讓可見和不可見的事物都變得可見。小說的「可見」是二維平面的觀看和顯現,而我們知道,把三度空間的事物投射到二維平面,必定產生變形、失真。此時就需要讀者透過「看」小說,以想像補位,製造第三維度來輔助小說的成立。
二戰後,美國的大學院校興起創意寫作課程,業經多年積累,大致可歸納出三大法則:「寫你知道的東西」(Write what you know)、「呈現而非講述」(Show, don’t tell)、「找到你的聲音」(Find your voice)(註1)。這套辦法能讓初學者快速上手,學習如何完成一篇夠水準的敘事。但小說不是科學,也不僅是說故事。好的小說常常在遵循法則之時也打破法則。因為小說渴望自由。
小說的奇怪在於,它既是極度要求組織、秩序的建制,也想要從嚴密監控的布局中逃逸。小說模擬一個完足封閉的小世界,有時開放邊界,讓更多異質的可能性自由流動。小說像一個聚落,小說也像一種無政府狀態。小說是極權統治的藝術,也是不受統治的藝術。小說總在矛盾的追求中產生巨大張力。
關於小說的趨勢
過去一年,世界如常發生不少大事。烏俄戰爭延長戰線、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爆發數十年來最激烈的衝突、全球疫情後的復甦、人工智慧ChatGPT華麗登場;台灣則有掀起波濤的#MeToo運動、總統大選攻防戲碼等等。正如事件不會自動依循日期、國界畫分,當代小說有自身場域的美學演變韻律,不一定與外部世界相對應。這裡試著從個人閱讀所及,提出近年趨勢的觀察。
首先是實驗性作品的稀缺。一九六○至七○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以反叛之姿登場,數十年來已獲學院典律認證。現代主義的技法、理念大多在時間中被吸收、消化成當代小說的基礎教材。當年以「破中文」或「小兒痲痺體」衝撞小說語言、形式的破壞性創新精神,沒有多少後來者。八○至九○年代興盛一時的後現代主義及後設小說,同樣後繼乏人。小說家似乎不再著迷於形式、結構乃至典故的文字遊戲。不過,當前方興未艾的母語書寫,也許正在鑄造新語感。例如外國經典文學的台語譯本漸次產出,或將拓展台語文書寫更多想像空間。(放諸其他領域,比如現今饒舌、客語、台語、原住民語音樂創作,已顯現充沛的創新能量。)
其次,寫實取向的公約數。寫實一向是小說寫作的基本功,關係到能否再現出讓讀者沉浸其中的世界。如何找到適切的敘事視角和聲腔,往往決定一篇小說的成敗(想想三大法則)。當前的小說似乎處在諸種題材的軍備競賽。題材如具特異性或對應特定價值、議題,常可吸引更多關注。例如往昔被壓抑的歷史事件、族群記憶,受忽視的自然生態,以及落在共同體邊緣位置的社群。或許書寫這類題材,不時得背負閱聽中介的責任,作者時常得強調「田野調查」的勞動和可信度,而作品以「好好說故事」為重,調降對於語言和形式實驗的追求。寫實取向成為務實的最大公約數。
第三,類型小說的借取。一般常以(純)文學小說與類型小說為兩大類別。類型小說含括推理、驚悚、科幻、奇幻、武俠、言情等類別,不同類型內部有各自的演化脈絡,有時相互交匯。類型就像標籤,分類需求是為了在大量出版品中被迅速歸類,以便瞄準特定讀者群。一九九○年代後期以降,大量翻譯文學被引入,年年有席捲市場的翻譯小說(通常是類型小說),像是強勢外來種,漸漸融為在地文學生態的一環。當類型作品成為作者養分來源之一,挪用類型元素也變得稀鬆平常。況且類型的邊防一向鬆散。如果一本純文學小說借取某些類型元素,通常也會被列入那個類型,反過來卻不一定成立(純文學小說的邊境控管較嚴格,關卡警衛眾多)。
近十數年最顯著的趨向是借取科幻元素。賀景濱、駱以軍、吳明益、伊格言、高翊峰、陳栢青、洪茲盈、林新惠等,皆或多或少披上科幻外衣,骨子裡仍是純文學。類型轉向的生發,也與外部文化環境有關。類型小說有其內在邏輯,小說先要達成類型要求,在地文史或社會脈絡並非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剔除掉讀者的閱讀背景負擔,類型相對有利於對外接軌、傳播及轉譯。此外,近年影音串流平台的興盛,引發內容的巨量需索,帶動影視娛樂產業尋找改編標的。而類型小說容易被辨識、簡報重述的特質,成為焦點所在。
以上粗略勾勒的三個現象,環環連動:由於著重挑戰、追問小說本質的實驗研發有限,寫實、再現的作品持續穩居主力區位。小說於是傾向追尋特殊題材甚或搭載類型標籤,以期望獲取更多受眾,超克市場考驗。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熱中文學實驗的作者本就稀少。實驗作品也不利於發表和競賽。實驗並不自動等於創新或衝擊,有想法也不等於執行得到位。實驗通常是個案,只有極少數能散播推展,形成風潮。實驗亦不必然外顯於形式,唯有保持實驗的內在精神,才可能做出一點不同的東西。當然小說也不是非得這麼嚴肅、講求創新。小說有可能只靠做好一件事,從生存戰場活下來:個人風格。風格指向區隔,帶來辨識度。有時風格恰好應對乃至塑造需求,有些故事、感受似乎就得用那些特定方式來說,甚至引發模仿衝動。大多時候,風格類似一種微小、頑強的抵抗,一種畫定個人話語領地的必要存在。
關於選擇的說明
雖然當今網路自媒體、社群媒介發達,類型小說線上平台盛行,文字如瀑流,到處都能撞見小說。以往的年度小說選,主要從報紙副刊、文學雜誌及文學獎得獎作品作為選取範圍。因為這些發表空間給稿費且保有一定程度的專業篩選機制,也因為它們仍是現今文學生態的重要組成,長年持守一方園地,理當重視。
關於小說發表空間的縮減,早在詹宏志編選爾雅版《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的序言即已提及。四十多年來,隨著媒體環境的轉變,情況只有更艱難。與此相對的是新世紀前後,各地方文學獎紛紛開辦,吸納不少小說產能。但這類小說由於獎項個別限制或規定,好些刻意採擷地方文史、地景的書寫,有時抽換材料也能成立。地方、校園文學獎小說普遍能見度不高,卻總是小說得以發表的機會,合計起來的數量難以忽略。儘管競賽有其利弊,起碼也經過寫作同行的鑒別。我從中選取了九篇文學獎小說。
十六篇小說的選取,來自一整年閱讀之後,一個瞬間的定奪。這份名單依編者不同心境有所浮動,但時間不允許我無限制地考量、猶豫下去。我的選擇偏向布賀東(André Breton)所說的:「要先去愛,以後會有時間了解為什麼愛。」(註2)我不打算強加這批小說一個整體解釋,也無法徹底解釋這些小說的所有面向。我傾向透過它們,多思考一點、多感受一些。
關於十六篇小說
高翊峰的寫作歷程是一部超微縮戰後台灣小說史。最初《家,這個牢籠》聚焦在本土家族內核、客語書寫,到《肉身蛾》散發濃郁的現代主義與城市氣味,再到確立風格的《幻艙》以一層薄薄的科幻盔甲包裹現代主義式的存在叩問,《泡沫戰爭》則穿上幻想外套說起寓言故事。前幾年的《2069》可視為近年科幻浪潮的代表作之一。小說設定二○二九年悠托比亞島發生裂島強震,受到四國共同託管五十年,卻在期限倒數十年,意外冒出自體演化的AI新智人。站在這個科幻宇宙延長線的四年後,〈T.E. 2073:莫卡卡與賽克洛普斯〉寫藝術家賽克洛普斯在退役的核電一廠駐園創作。全篇登場角色、對話,皆如器械擬造般生硬、淡漠。僅存的人性溫柔發生在賽克洛普斯與實驗猴莫卡卡之間。
藝術家以繁複的積體電路、金屬骨架打造名為「悠托比亞時間」的裝置。材料回收自人造巡護員殘體零件。賽克洛普斯正如其名,重演獨眼巨人在神話中吞吃人類。只是這一次,他使用的是在鎮壓革命行動中壞毀的人造人。充滿大小晶圓、齒輪管線交疊的作品,彷彿獻祭。完工後,賽克洛普斯往外尋找實驗猴。小說收束在藝術家像猴子那樣四肢著地,快速奔跑起來,暗示著猴與人也許相距不遠。小說英文篇名Macaca & Cyclopis,拿掉中間像是晶圓裝置的連接號,就是學名Macaca Cyclopis的台灣獼猴。
高翊峰像個專注的鐘錶老師傅,執迷於打磨不同時間形態的精巧構造,細細琢磨那一切微小、精密的零組件,使得小說本身就像精緻工藝品。整篇小說像在探問:即使你如何處心積慮調整、重組、凝結時間,最終時間仍會吞噬你曾有的抵抗和叛逆,軟化堅硬意志,讓你從理性到近乎機械的狀態,復返到感性乃至獸性的那一端。演化不一定朝向直立,也可能四肢著地。
林冠彣的〈SW33T REVE-793.AVI(本文由ChatGPT產生)〉帶來激爽的視覺奇觀。起初只是肥宅在清明掃墓空檔,躲進公廁看片尻槍,遭到無端降下的鐵捲門關便所。詭譎氣氛急轉髮夾彎,一路奔向爆漿橫流的極致唬爛。這是篇讓讀者吶喊「我他媽的到底看了什麼」的小說,也是篇混合後設、科幻與末日色調的小說。儘管這類「我意識到我被更高存在所操控」的哏並不少見,但對應當前生成式AI的快速普及、人們檢索關鍵詞的習性,小說展演一種逆反情境:字詞標籤倒過來控制了我們,娛樂了更高存在的祂們。覺醒的自我意識,困在高潮過後的末日孤獨,試圖尋找反擊方法。讀者千萬別給滿載褻瀆、下流的詞組遮蔽—搜尋是採集本能的電子形式,而情慾是繁殖的糖衣。色情多到爆炸反而減低了色情感。小說不僅以大量關鍵字訓練另一次元的神,其實也在訓練讀者習慣、趨於無感。於是小說的內核袒露出來:渴望結合,渴望有所連接,渴望情感和肉身同步。既然不被了解,只能怒嗆一死,結束這一輪。
關於不被了解的孤寂,陳莉文〈安靜的轟鳴〉近乎完美演繹了當代的頹廢狀態。這句判斷有語病:我怎麼知道當代的頹廢是什麼狀態?但這篇小說寫到讓我「覺得」對那樣的狀態有所體會。敘事者「我」渾渾噩噩混到大五延畢,只想躺在狗窩般的房間,就連尿意上漲也要沒意義的忍到不能忍為止。明明沒什麼事也什麼都不想做,卻一直覺得很累很煩很厭倦。一種近乎憂鬱症的癱瘓心態。
「我」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她曾經為了一個偶然的眼神而燃燒自己、精神奕奕過一段時間。只是人無法靠著不斷回憶那想像出來的微小火花,持續揮霍積極起來的動力。廢材宅女鎮日窩在房間,滑手機消耗光陰也可以叫外送填飽肚腸,還裝死不回訊息。如此完美小世界,卻意外破了洞。她從洞口望見自己與他人的落差,湧出恨的能量。小說並不認真指控原生家庭的創傷,而是迂迴地透過世故、尖刻自嘲,來鑽破名為自我的硬殼。
小說似是郁達夫〈沉淪〉相隔百年的遙遠回聲。也像宅男小說家森見登美彥一再演示的:所有妄想都在腦中發生和完成了,只是沒有行動。沒有見證者的生活像是不存在,最終「我」走出了房間:「我不要再這樣下去了。」
李金蓮以〈許老師的閱讀史〉寫出愛慕的似有若無。小說中的許老師長年默默承受著生活。許老師這個稱謂帶有疏遠的距離,像她在母姊眼中,沉默而古怪。她曾是代筆寫手,以姊姊的第一人稱對未來的姊夫說話,不知不覺把某些心意編織到書信裡。小說寫及閱讀與愛情的相似。擁有一本書,會產生占有一本書的錯覺。只有透過閱讀,才會真正占有書。那是排他性的占有,類似愛情的獨占。那是有一隻手從字句間伸出來跟你握手,在文字間交談,情愫發生。寫信和收信兩造是彼此的讀者和作者,他們需要互相對照、查閱才能理解對方。有時,這樣深刻的理解,必須存放在一個誰也看不到的深處。然而含蓄、節制的情感,在時間深處悄然生長,重到許老師難以承受。幸好她已經花了大半輩子在練習承受生活。
張嘉真的〈棄兔〉也與「代筆」有關。對照今年從政治幕僚職人劇《人選之人—造浪者》引爆的#Me Too運動,這篇小說飽含曖昧、模稜兩可的思慮。小說透過兩種字體交叉編組,也在第一人稱「我」與第三人稱「她」之間往返,造就後設意味的懸疑:究竟這個讀著「我」的敘述,且跟朋友夾敘夾議的「她」是否同一人?
師生關係放在校園場域,總有權力關係不對等的傾斜。在小說推演過程,卻不見得必然倒向看似握有更大權威的師長。受害者與加害者並非截然二分,有時亦會顛倒。儘管最終作者給出確切的謎底,但小說的形式設計上,其實提示了逆讀的可能:「她」也可能是書寫著「我」的人。她也許是虛構老師假冒她寫部落格,而虛構的復仇故事。因為我們知道作者是寫下「她」和「我」的故事的人。
黎紫書帶來重層虛構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標題致敬小說家褚威格(Stefan Zweig)同名小說,也同樣以書信作為小說主體,述說一個來自過去的幽靈,也許是小說的幽靈,上門追討債務。小說大意是某美國華裔女作家收到一封以打字機打出的英文長信,引發作家的信心危機。因為這個陌生女人與她細細討論了她山寨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中文短篇小說。小說以第二人稱「你」起始,把第一人稱「我」交給寫信的猶太老婦,形成微妙錯置。來到小說後半,「你」與「我」的換位,張力加劇。小說藉老婦滔滔之口,洩漏小說家如何拆解文本的工夫,也顯露小說家如何反思自身的寫作。小說曲折透過兩個小說真假文本(實際存在的鍾芭.拉希莉作品vs.僅在小說中轉述的山寨版),直指文化挪用、語言壁壘的弊病,探問跨語剽竊的倫理問題。小說不止如此,它更進一步逼問著寫作的本質。而這,就像小說中凝視著自我的監視器鏡頭,揮之不去。
同樣是書信小說,林佩妤的〈桃子〉指向一個收信者暫時缺席的獨語狀態。底層女性可以說話嗎?這篇小說大膽冒著僭越代言的危險,讓她們述說自己的故事。小說以第一人稱而不以第三人稱,凸顯敘事者「我」的主觀感受。文本雖以華文寫就,文句的簡短、直白,既模擬翻譯腔,也對應印尼籍看護「我」的階級位置和聲音。
小說沿著時序的書信串成,呈現「我」在時光之中的遭遇和感悟。這些不寄之信是「我」的隨想手記。「我」把自己藏在一封封書信裡,謎底漸漸揭露:她與前雇主家庭男性發生關係,懷孕生下孩子,必須寄放在機構中。而她自己則以逃逸移工的身分繼續在另一個家庭工作。「我」的藏匿與封閉,加上疫情肆虐,世界更形內縮。但同時,小說中的「我」並非被動等著事情發生,而是穿行在不同場景,尋找調整命運的可能。
他者的命運可能很久以前就發生過了。朱嘉漢的〈L’oubli〉寫十九世紀末的越南廢帝阮福明被法國殖民者丟包到阿爾及利亞,從此說起了法語,變成一個風景畫家。他一生的功課就是盡可抹消自己的存在。即溶咖啡似的溶入澆頭而來的命運,沉澱在歷史深處。這是一幅怪異的肖像畫,只有簡筆勾勒輪廓的線條、多層疊加的白。然而正是那些刻意的空白,才能顯影阮福明的存在本質。
這篇指向景框外邊的小說,探問著遺忘是什麼。一個被放逐到外國的君主,如何在異鄉,介於人質和瀕危物種的處境下度過餘生。他刻意遺忘自己,人們也在遺忘他。小說使我們停下來思索:我們如何理解他者?尤其是那些被廣漠時間吞噬、消化的他者?身邊的他者有時住在家裡協助你清潔衛生,有時在郊區鐵皮工廠裡揮汗打拚,或在工地鷹架間搏命工作。至於那些看不見的、更遠的他者,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們與我們之間的關係?
伊森的小說從一開始就認定他人無從理解。〈一坪的森林線〉起始於健身教練和會員時常卸下身分,在小房子裡裸裎歡愛,一對一的教練課。他們內裡包藏著脆弱的心,嫻熟切換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名字是一道簾幕。身分是另一道簾幕。小說中的城市男女切換角色,俐落得像在切換社群小帳。安於表面、不要追問是基本禮節。日日繁複運作的前後台,難免露出破綻。原本共享部分後台的男女,在其他舞台情境中巧遇,困在多重舞台上的演員不得不敷衍尷尬。而這些與大安森林公園二十四小時實況直播的鳥巢動態形成對照。他們一起看鳥的房子,個別看別人的房子,分享一個暫時的房子。他們曉得,租來的東西,遲早要還。
一個不怎麼了解自己身體的新手學徒,出現在施雅文的〈感官的模具〉。小說的「我」懷抱心事到台東的陶瓷工作室。天寬地闊的悠緩敘述,不經意逐步揭露自身訊息,像是模具的翻製和注漿,一個細節、一個步驟耐心寫出。看似平穩如鏡的敘事聲音,牽引讀者去看、去感受、去觸摸、去嗅聞,像是在跟主角同步體驗這些感官的幽微變化。隱隱有哪些不對勁。讀者可能察覺,小說尾聲精筆細描如夢似幻,大霧充滿的場景,彷彿浮現空中的肺臟胚體,有那麼一瞬超脫現世,像是整座城鎮以「我」為器,澆灌著無以名狀的紛繁感受。小說以人物之口說,土擁有自己的記憶。小說也告訴我們,人可能記得很多,但身體記得更多。就算身體有點壞掉,也要謝謝身體。
Apyang Imiq (程廷)有個關於大腿的故事。〈大腿山〉看似老掉牙的原住民少女下嫁外省老兵敘事,在作者手中有了變形。小說焦點,落在少女面對情慾的扭捏心緒,而把外省老兵壓縮到背景。「大腿」與「山」在太魯閣語都叫Btriq。那是「三角形的山,山的形狀從尖變鈍,從細變寬,寬得必須用手張開來擁抱的地方。」這篇小說的視角亦是如此。不從時代大事談起,而從少女心事切入。所以故事要從少女重返大腿山開始說,從寬變細,從鈍到尖。少女被迫以性換取經濟,在那樣的交換中,她被縮減為充氣娃娃般的存在,無聲而沉默。但她記得身體細微的震顫,不該只有簡化的交合。少女回想起軟玉的溫潤、冰涼,也想起許多尖銳的樂趣。她只是還沒準備好怎麼面對。
也有人面對情慾像沒在面對。偷筆的〈聖水〉筆觸充滿濕黏的蛋白質腐敗味。敘事者「我」跟一起用藥嗨的兼課老師「上動物園」,摔進糾纏不清的性和愛,讓「我」時時處在焦慮。小說動力就在「我」如何掙脫爛生活的焦慮。但焦慮和浮躁,透過生物教科書式的描寫,有如「動物星球」頻道的旁白,四平八穩,反倒讓焦慮無所不在。尋找「聖水」的行動包含神聖和褻瀆。為了尿檢過關,找人一同發揮獸性,偷取他人尿液(剩水),幾經轉折,受到來自宮廟和家庭的「聖水」淨化。
如果稍微從敘事的「我」退後幾步,讀者也能察覺到,「我」早就淹沒在焦躁和藥癮而不自知,變成一個不太可靠的敘事者。幻覺和執迷在他腦中交互出現,他以為能瞞過他人,其實破綻百出,而他也將被扭送到另一座充滿柵欄的收容所嚴加看管。
陳建佐對宮廟有話要說。〈離島〉坐落在大島旁的小島。島的封閉性時常透過尺度展現,愈是窄小愈是緊縮。如此閉鎖環境,迫使人在過度靠近的關係中摩擦、受傷。小說框出的社區即景,宮廟維持許久以來的中心地位,人際網絡圍繞著信仰依序擴散,而被附身的乩體,多了一層無法測量的神靈,神與人之間的糾葛,也增添人與人之間的糾結。作者萃取在地台語氣口,展示新舊並陳的當代景觀,扶鸞唱乩對照周圍看客手上的智慧型手機,靈附乩身遊於人間,人滑手機上網閒晃,同時出神。
年少的黃宥茹知道酬神慶典是怎麼回事。〈扮仙〉寫高中生「我」以北管嗩吶為引,游移在現實世界與民間信仰的夾層。在這樣的年紀擁抱嗩吶,意味著與其他同輩切分的孤獨。「我」太年輕,尚不知曉許多過去,她只是飄來飄去,跟著身旁的長輩,接受一個沒有北管嗩吶哨片專用盒的文明世界。
因此小說的珍貴品質,在於她縱有矛盾,依然沒有閃躲、直直面向現實。那是宮廟科儀、樂音與不停流動的城市景觀混雜交織的喧鬧現實。那是固著與變遷的地景狐步舞。快慢交替,新舊輪轉。都說「扮仙」是正戲開始前的祝福儀式。對於懷抱著紛雜心緒的「我」來說,之後的人生才正要起步。
族群記憶有時要以特定的語言來說。張郅忻的〈打拳頭〉就是如此。如果這篇小說以全華文寫就,只會是一則練武往事。當客語成為敘述語言,像戴上陌生濾鏡,觀看小說如何透過兩兩成對的練拳少年,呈現客家生活方式幾十年來的變遷。打拳防身、禦敵抗侮曾是拓墾時代客家庄的要事。小說開場的九○年代,客家拳傳人已是瘦弱長者,眼睜睜看著客家拳從實用變成象徵。回憶在拳腳招式中開展。老人幼時,跟著小叔叔到家族大屋學拳三個月,以便回村傳給其他人。過往務農為主的生活,鄰里家族關係緊密,團結對外。遇有閩客爭端,政府管不了,就得自行靠拳頭解決。然而功夫和農村也抵擋不了社會轉型,皆不分族群沒落了。老人與族兄的宿命,換了個時代繼續在不同後輩身上重演。拳頭仍是拳頭,只是變成繡花噱頭。
獨特的文體風格像是外語。二十年前,童偉格出第一本小說集之時,彷彿是寫作已久的成熟小說家。近兩年,他在雜誌上連載的專欄「拉波德氏亂數」,近乎不可思議地以每月一篇產出。這系列文字令人想起他十年前的《童話故事》:時而說故事,時而抽象論述,時而文學批評,神奇的是,這些扞格文體鍛造得渾然天成,自成一家。童偉格的語言密度、探索形式和思考極限,乍看澹遠深奧,實則頗為激進。
專欄連載途中,沙林傑、索爾.貝婁、普立摩.李維、阿摩司.奧茲、因惹.卡爾特斯、菲利普.羅斯等猶太作家接踵而至,逐漸收攏在思索「猶太大屠殺」問題。為什麼要看童偉格思考猶太問題?因為只有夠深入理解他人,才能深入認識自我。童偉格出入於作家與作品的虛實之間,探究猶太作者的書寫與存在,專欄最終以出身巴勒斯坦的愛德華.薩依德總結,別具深意。
此篇〈林中空屋〉聚焦在法語猶太小說家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拚命寫著《法蘭西組曲》的最後時光。小說寫著內米洛夫斯基透過速寫契訶夫的一生來觀照自身寫作,簡要擷取她短暫生命的片段,自由穿梭於她作品段落。全篇看似沒發生什麼事,但讀者知曉,恐怖滅絕正在發生、已經發生,那些難以言說的感覺,被定格在最接近滅絕、美得毛骨悚然的林中空屋(註3)。
拉波德氏變色龍生活在非洲馬達加斯加島,一年一生,有如昆蟲或草本植物。牠們在雨季的短短幾個月間,完成孵化、成長、競爭、交配,然後集體死去。這個物種無法活著看到下一代,但生命持續往赴循環。幾年前,失蹤百年以上的「沃茲考氏變色龍」重現足跡。據說牠們是拉波德氏變色龍的近親,以同樣的生命迴路存在著,以致長期沒有發現紀錄。
小說也是奇怪的物種。小說需索讀者貢獻時間和想像力,協力創造專屬體驗。小說追求差異,難以複製,卻可彼此連結成不同版本的系譜。每年都有巨量小說產出,每年都有一本年度小說選。大多數小說的生命週期短暫,就像這兩種變色龍那樣默默存在,默默死滅。只有極少數小說能抵擋時光的滂沱大雨,留存在讀者心中。但只要你開始看起任何一篇小說,那篇小說就會被喚醒,再度活了起來。
註1:創意寫作的三大法則來自Mark McGrul, The Program Era: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譯本參見馬克.麥克格爾著、葛紅兵譯,《創意寫作的興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2)。此譯本有大量刪節。
註2:轉引自安妮.艾諾、費德里克─伊夫.吉奈著,許雅雯譯,《如刀的書寫》(台北:啟明出版,2023),頁122。
註3:本篇選文為專欄版本,收在集結成書的同名篇章經過作者重組改寫。全書架構安排、內容也不同於專欄刊載順序。參見童偉格,《拉波德氏亂數》(新北:印刻,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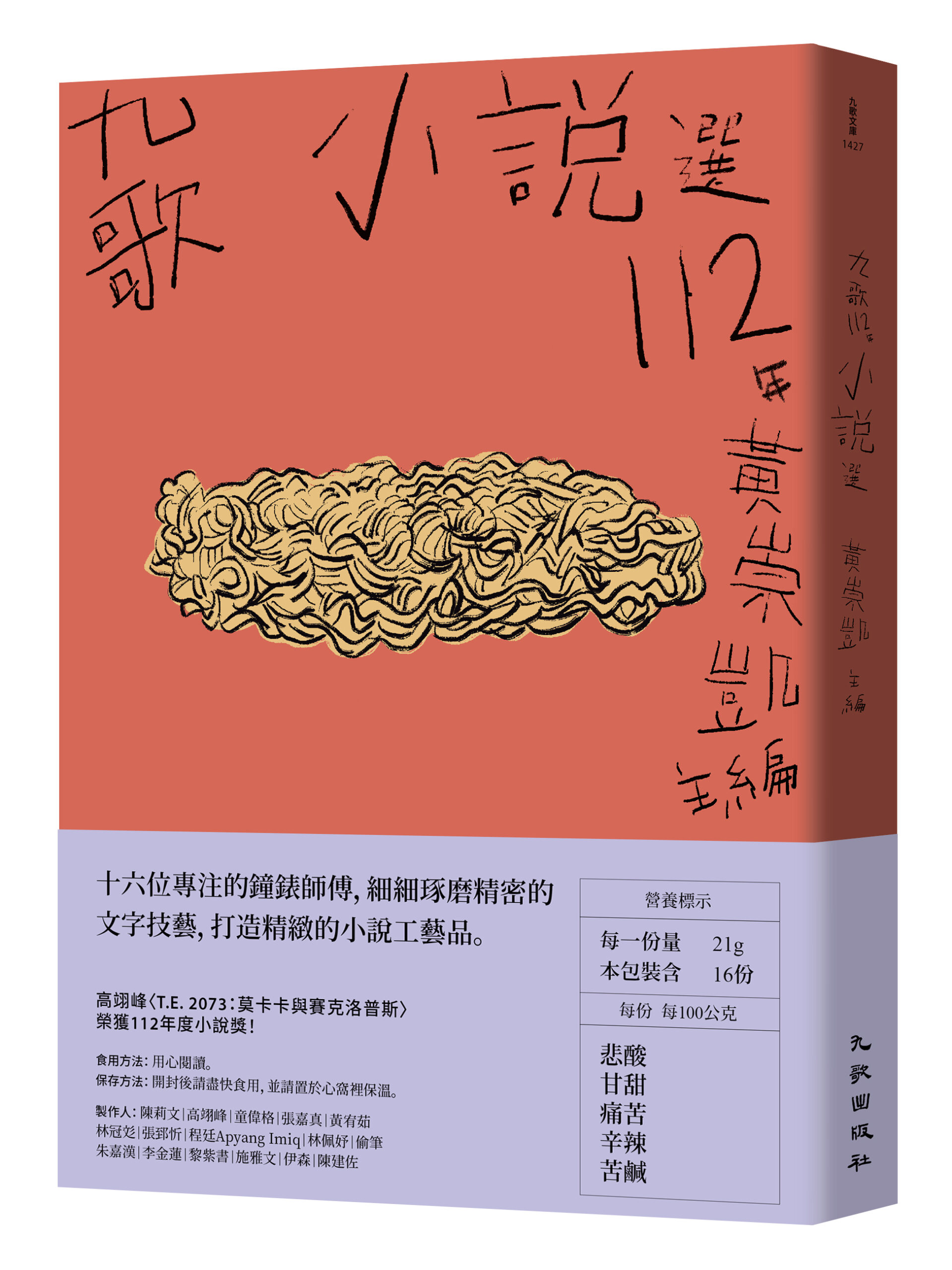
《九歌112年小說選》
攝影/汪正翔
|主編:黃崇凱
台大歷史所畢業,曾任耕莘青年寫作會總幹事。做過雜誌及出版編輯。著有《字母會A~Z》(合著)、《新寶島》、《文藝春秋》、《黃色小說》、《壞掉的人》、《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靴子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