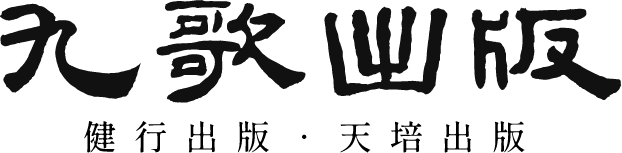關於陰影的技藝──言叔夏主編《九歌111年散文選》序
相較於小說所造就的技藝迷宮──那由繁複的工藝、零件與材料所結塊增生的地下根莖(小說的密室?),以及往上發芽攀出的甬道與樓層,散文的「技藝」似乎始終難以真正「疊高」?它如同透明布幔,覆蓋著經驗世界的凸起與凹伏。因而它的輪廓曲線有絕大比重早就被經驗先行決定了。即使它再如何振作,也終歸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經驗重述者。這裡之所以拿小說作為對照,不能不說沒有近年來在各大文學獎的評審場合裡文類界線間的模糊已愈趨普遍,蔚為常態的理由。如今的散文也說故事,也天工開物。剪紙小人栩栩如真。有時它甚至虛構滋事,並且──在評審的場合裡,這種虛構(在技術的範圍內)其實也經常被默許。
但這二者在文類的核心似乎還是有一點根本性上的不同。就好比在散文評審的場域上,一篇挪用了小說技法而勝出的作品,放到小說的擂台上,我們忽然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二者筋數皺褶的不同。這裡說的並不是孰優孰劣,而是文類的物質性,主導了它們作為一種技藝的極限與形態。能不能虛構其實不見得重要。在小說裡,命運機器中的機關之物才是核心。小說家指認旋鈕,鍛接因果迴路。換句話說,那其實是一種在「必然」與「偶然」之間撐出一個異次空間的技藝。而「散文」呢?「散文」似乎只能恆守一種「必然」?在事件廢墟的瓦礫邊上,它即使調度故事,重述情節,都難以免去所有投擲將被時間沖刷進下游的沖積扇。人無法踏進同一條河兩次。這或許就是為什麼在大學或研究所的課程結構裡,「小說課」似乎可以逐年級一開再開(或被包裹在各種「創作與方法論」、「寫作理論」的課目裡,實則它們的對象文本往往都是「小說」),它的繁枝密林彷彿永遠存有探勘的可能。如同圍棋棋士的段數疊高。同一個故事說上一千零一夜,它始終有它自身用以擴充的差異與重複。而「散文課」卻通常是一次性的;我常常在星期四早晨九點鐘的研究所散文課上質問起自己:「有必要在這些早已嫻熟寫作技巧的研究生之中開這樣一堂課嗎?」當我們圍聚在一堂散文課上,我們討論的是什麼?他人的經驗?思索的軌跡?不幸的幼年?難以突圍的現在……彷彿那些經驗,就是技藝本身?
這並不是說經驗的高光強度反過來可以決定散文技藝的段數。如果討論一篇散文如同討論他人生命經驗之厚薄,那對作者未免也太冒犯(雖然在某些政治正確的先行主導下,某些作者可能不介意這種冒犯)。幾年前我曾在某個大型文學獎的初審裡讀到一篇來自監獄受刑人的文章,那文章裡有常人無法經歷的人生:持槍、販毒、逃亡、殺人……但這篇稿子至今仍令我難忘的地方,並不是這些經歷本身。而是這個自稱從沒拿筆寫過什麼字的作者,或許正因摹字多遍,這份以五百字稿紙謄寫、長達八頁,將近四千字的方格裡,每個字底下都隱約可以看見前一次謄寫力道所留下的隱形字跡:他可能已經重寫了第二遍、第三遍了……他是否會有一個瞬間,從字詞所描述的事件中掉落出來,並且忽然發現了這些前次所留下的痕跡呢?像是所有前一次所分裂出的暗影:一旦盯著同一個字注視愈久,字也會生出它的另一張臉來。
對我而言,散文如果與技藝有關,那應是一種關於陰影的技藝。就像立下日晷觀測太陽運行的方法;最後我們得到的,其實是一張關於陰影的紀錄。經驗如果是一種白日運行的太陽,那麼散文裡的「自我」會是那支竿子嗎?有些太陽沒有透過陰影是看不見的。有意思的是,這個文類向來是「自我」的領地。它的第一人稱「我」與作者幾乎是先驗性地疊合在一起。但散文裡的「我」是否真是這樣臣服於經驗的呢?我想那並未必。我一直認為這個文類的運行邏輯是一種類似操偶劇裡操偶者與人偶之間的關係。在這個獨白的舞台上,人與人偶既是同一人,也不是同一人。他們像是人與自己的影子那樣彼此補釘縫合,隨光源的角度強弱延長或變短(故這些暗影有時也會被黑夜吞沒,沉入無能象徵化的潛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散文」或許並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麼透明?當「經驗」成為「經驗」的影子,「自我」是「自我」的陰影,這個看似只是輕輕覆蓋著經驗世界的文類,其實設下了一層又一層透明的薄幕。為了一種裸露的掩藏。
或許,也就是這樣臨近經驗與自我之暗影的散文,在這過去的十年裡終於迎來了一個它或許未曾料想過的時代。當我們與日常經驗的關係在至今約莫十年前逐漸轉移到一部掌上手機,新的光源似乎重新為我們定義了「自我」及其所投射的竿影之間的關係?過去一百年來現代小說窮盡其技藝所欲展示的各種萬事虛構因果,而今似乎毫不費力即可在網路上抵達這種多視窗的共時性平台(有些當代小說反倒因為現實經驗這種高強度的虛構感而遭遇了它技藝上的挫折)。就好比近年已流傳好一陣子的一個詞彙叫作「人設」。當這個在臉書粉絲頁上應該自我標註為「虛構人物」的「人設」走進各種視窗,我們的日常究竟是一則虛構小說還是一則散文?(有一天我們也會在《文學理論》裡讀到「人設」這個詞嗎?)在散文的領地裡,它所遭遇的是:經驗的共時性或許亦正在搖撼過去漫長時間裡那堅不可摧的「自我」表演場?頂上光源八方而來,事物與自身的疊影朝向不斷打開的經驗邊界(那些快得幾乎沒有辦法用手去指的經驗世界)。近年來散文的潮間帶經常漫漶至小說,我倒不覺得全然是散文可不可以「寫得像小說」的問題,而是我們今日所面臨的經驗世界本身,早已挪移了過去我們對「虛構感」的量體指標。誰都可能在誰的現實視窗裡成為一個(真實的)敘事/虛構人物。
然而,就像某日午茶間工作上的某同事說起報載不久以後人類就可以出發火星旅行。「去一趟單程只要八個月簡直是郵輪之旅。」眾人驚呼啊真的嗎。未來搞不好學生畢業旅行都要去火星。另一位同事(忽然以永澤口吻)說:「問題是去那裡我們要做什麼?一直看那些重複出現的隕石與岩層嗎?」當我們活在一個連火星都可以抵達的時代,最虛構的經驗也許並不在八個月以後的另一座星球,而是我們心中真正渴望的那個人,那件事,那個地方。因為那裡最遙遠,需要太陽和它的陰影作為發射的能量。沒有在自己的心中立下一根竿子,是到不了的。
◆
以上種種,是進入這部散文集以前,來自我非常個人性的隨想或提問。我想或許所有年度散文選的主編都曾想過這個問題,關於一部以年為單位的文集,它的邊界與向度,究竟在哪裡?去年接下這個工作時,我私心希望這本文集裡所收錄的作品能成為這一年來經驗世界所投射下的某種日晷的痕跡,標註著我們曾共同擦身的具象或抽象時空。在成書的過程裡,也一直希冀能打破早年散文常見的某種以主題或類型來分類的編輯方式,故初始也是天馬行空,(小小的)野心勃勃。恰這兩年或受網路社群發文型態的影響,副刊與雜誌刊載千字以下的短文特別多。而從前幾年開始,臉書文章亦已有被收入年度散文選行列的前例。此次本想獨立闢出一輯,只放各種四處蒐羅來的短文,而且最好只有這一輯橫排右翻,不是很像專放珍果寶器的十六格抽屜櫃嗎?當然這個方案後來沒有成形(感謝九歌的編輯張晶惠小姐一直被我煩)(野心很快熄滅!)。然而,在為這些短文進行抽屜分類時,我發現這二者如果拿掉出處,其實並不能分出哪篇出自個人臉書、哪篇出自紙本副刊雜誌。有趣的是前者覆蓋後者的領域大抵從二、三十年前還有「網路文學」這一古老詞彙的個人新聞台時代即已開始,後者由於近年雜誌平台或也經營臉書或IG社群的緣故,有時反而會在紙本上讀到一篇「咦這好像也很適合出現在臉書」的短文。話說回來我們究竟是被什麼所限定哪些載體該有怎樣的文字而哪些該被排除呢?如今我們的生活其實早已慣於多視窗運作。雲上雲下,物質材料與抽象平台的杯觥交錯,也會翻生出一種全新的感覺結構罷。無論如何,這些如同稜鏡般的剔透短文如張惠菁的〈清明/背耳與嬰兒/機械鳥之冬〉、江鵝〈過彎/安德魯〉、黃麗群〈台南的食物/吃瓜〉、隱匿〈百元理髮〉,都是琉璃珠般的一花一世界,每次重讀,都像搖萬花筒那樣可以重組出不同的圖案。同屬短文串聯的組曲,韓麗珠的〈只有耳朵,沒有嘴巴/錯置感/穿在身上的氣氛/沉默之膜〉則像是作者為自己鑿開的洞穴,可以理毛可以自我清理;若對照香港的現實,它們或許還有防空洞的意味。
而同樣錄自臉書,黃家祥〈直男的研究〉是難得的第三人稱自白體。這個其實很少出現在「散文」這一文類裡的性別身分(或許此一文類與此一身分的性質本身就存在著互斥的張力?),現身與自我表述的方式該循何種路徑呢?當代的「自由」,其實是由邊界所決定的。李欣倫〈頭朝下〉精準而又尖銳地刻劃出女性婚姻生活中的各種圍籬與界限。劉大芸〈人體模特兒、神韻的物理規律與疤痕海豚〉裡關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走位、顏一立〈暑假〉裡的「自由」是自己超渡自己的一部心經?自由從來都是折射的。我也喜歡方郁甄的〈母狗〉在看似濃烈乖張的敘事裡其實充滿強烈的思辨性:性、性別與身體的對位關係裡,那掉落出來的毛邊是什麼?許多事物,是如同野獸一樣沒有語言的。也許在這篇文章裡,「自由」本身就是一隻這樣的野獸。而關於「自由」的問題,來自中國的作者張笛韻〈自由〉說得最直白:「五米是我願意讓渡的全部距離。」
生活裡有五米的自由嗎?五公尺,在日常生活裡是五倍安全社交距離。去年的散文竟有許多篇談及二、三十代青年的職場生活。黃昱嘉〈鴿籠〉、黃胤諴〈求投餵〉、沐羽〈隔間裡的Bullshit:兩部平行的上班族歷史〉,精準而靈巧地描繪了三種工作場域。有意思的是這三位作者行文間都(十分誠實地)自帶「隔板」,抒情與觀測之眼並具,自帶五倍的安全社交距離。陳允元的〈浮浪〉是四十代的另一種煩憂。以平實之筆觸,書寫北漂前中年世代的台北旅居浮浪生活。唐捐的〈神經衰弱自療法〉裡,指引五十代此輩離鄉背井、一去不返的前方路標,竟仍是詩(或者鬼魂)。房慧真〈還想再多看一點〉則是以城市田調現場的觀察者之姿,凝視各種底層生命經驗的最前沿。周芬伶去年出版散文集《隱形古物商》,書寫自己蒐羅古物舊物的癖性。〈神的凝視〉行文寬綽而有餘裕,是其中保有一種微妙幽默感的篇章之一。
散文裡蔚為大宗的家庭素材,本已是個一寫再寫的場域。然或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在世界歷經重新換血的這段期間,這一年的作者們給出了陰影面積等同陽光面積的作品。夏夏的〈新生〉、江佩津〈迷你倉〉、洪愛珠〈巴黎野餐〉、田威寧〈時光電影院〉、李屏瑤〈跪姿練習〉、馬尼尼為〈我現在不跟你道晚安〉、陳柏煜〈在和室裡〉等,或道別,或練習共處,彷彿回應的是我們大而殘破的生命本身。而二○二二年也是一個從過去投遞而來的時光膠囊嗎?孫梓評與湖南蟲的往復書簡〈重抵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陳宗暉〈我們快樂地向前走〉、張經宏〈在路上〉、李桐豪〈走在一場電影裡〉是來自過去還是投向未來的書信?又或者它們其實是公路旅行上車廂裡流洩出的歌曲。唱片或膠捲上的土星環帶,銘記著一圈一圈的刻紋。這些來信,都延宕了散文鐘面上的某種「必然」,將時間的向度無盡打開。而郭熊的〈發自山林的情書〉則是從台灣心臟之處的山林裡發寄回來的心跳聲響。那些深林裡的風鳴獸走其實無比抒情,本身即是一封不言自明的情書。
有些經驗充滿編碼與名字。它們就如同一支軍隊在路上,搖旗張鼓要去一個戰地還是遊行隊伍?楊富閔〈一支軍隊在路上〉、吳妖妖〈煙囪養大的〉、許恩恩〈薄荷胭脂雲〉都是這樣分別從偏遠畸零地出發的一支軍隊(不管那是具體或抽象意義上的)。或有歷史地誌之縱深,或途經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現場。而陳尚平〈在末日之後與保護膜的悲壯相遇〉則以另一種學科的眼光回來檢視我們被包膜的世界,究竟「保護」了什麼?蕭詒徽〈如果沒有夏宇,誰剪碎那些可疑的雲?〉告訴我們,大寫文學史的轉彎處常遭彗星撞擊,文中那彗星就是彷彿橫越光年而來的詩人夏宇。我們難以忘記當年她乘噴射機離去,噗噗留下噴射雲朵。她也帶回了一支軍隊嗎?那麼這支軍隊應該是由一匹剪碎的雲所組成的。
有些經驗則不屬於任何名字。如同散文這個文類是如此地像生活裡指間流逝的水,無法掌握,有時根本不用掌握。我們都知道有種經驗既屬於午夜也屬於午後,既屬於日常也屬於危險。那或許就像是柯裕棻〈險境〉裡一趟與母親的公路旅行,所謂的險境之險,不就在於它什麼也沒說,卻什麼都說了?王麗雯若無其事散步的〈動物園〉,那些圍欄動物們也有屬於牠們的快樂嗎?崔舜華〈臉盲〉是如何穿過一張張密麻相似的人臉而找到自己的臉的呢?林薇晨〈沙龍碎記〉裡打磨得圓滑的指甲,也曾是在心上留下過一道指爪的(啊這真是一篇溫暖的文章);以及鍾怡雯那被覆寫在大疫前景的日常生活〈這樣也很好〉。所有難以言明的,這樣就好;這樣也很好。
◆
本書的集結必有主編個人的偏好,亦必有因各種因素而無法收納進來的作品。最物理性的原因如黃瀚嶢〈巴拉草〉或簡媜〈你也有銀閃閃這一天〉,都是長達一萬字甚至一萬五千字以上的極好佳構,然因書籍篇幅量體有限,最後只好放棄去信徵詢作者意願。又或者如安溥〈跨越新年〉發表於私人電子報(寄給我這篇作品的友人表示這裡面有一顆大珍珠)、楊莉敏去年唯一發表的〈洞〉則是一篇長文裡破碎的一小段、陳栢青〈我想跟歐普拉一樣去見伊麗莎白‧斯特勞特〉、林蔚昀〈在飛彈下做早療〉等等,凡此種種,因整體編排等因素,亦只好打消去信詢問作者意願的念頭。我雖對未能將之收錄進此書感到抱歉,但又覺得或許有些文章正是用來在晴天歷歷的一人大路上與它當面交逢的。那是一些像是命運之類的東西。我一直相信人與文字之間有一種神祕主義的關係,類似桃太郎在路上遇見的三隻動物。如同年輕時在一座無人圖書館的書架深處遊蕩,一本書有一本書被遇見的方法;你不必通過我,你一定也會遇見它。這一年來我試著把自己變成一台google收集器;因為這個工作,我有一個專門用來轉載作品的臉書私密社團(團員只有我一人)簡直石器時代的原始人出門狩獵回來那樣堆滿各種貂毛動物。深感在網路社群的時代裡,能有這樣靜定的一年,被這些暫時圈養的多毛動物們親密包圍,一起待在一個隱密的岩洞裡過完冬天,是這個工作帶給我的無上至福。
二0二二年是舊世界與新世界之間陽光普照的崩塌地。大疫成為常態。日常與非日常的界線逐漸消弭反轉。我們似乎正在練習一套全新的指認世界的方式?當我們對著一方螢幕中的遠方頭像們開會說話,上課下課;扭熄視訊鏡頭時,一切戛然而止。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鬼魂」這個詞?當我們按鍵叫來食物。我們與食物還有那位一期一會的外送員是否又將重新演繹起百年前佛洛伊德fort-da的迴路?經驗。經驗。與經驗。分不清究竟是鼓錘還是鼓點的經驗。去年在國際書展的講座會場,有一位讀者提問:「我們為何還需要一本年度散文選呢?」啊二○二二年的我是否真能回答這個問題?在這個「我們」變得可疑的時代,我們與書的關係如此千絲萬縷又如此一目了然。當「我們」走進同一本書裡,「我們」究竟得到了什麼?一個他人經歷的下午?一段被紅筆來回畫線的句子?還是一張社群媒體套過濾鏡的硬筆鋼手寫字?你會在沙漠裡選擇攜帶一本年度散文選還是一部可以呼叫Uber的手機呢?在這個3D列印早已可以複製拖曳出一整座城市的時代,如果我們還需要一本年度散文選,那或許只是為了將那些指間消逝之物列印出來再把它一頁一頁撕下吃掉。如果記憶也可以變成一片吐司。一本《追憶似水年華》跟一片小瑪德蓮究竟孰輕孰重?無計可施的時候,我可以吃掉你的胰臟嗎?重要的是,你飲的鴆都來自你的渴。而你的渴,就是你的世界開始的那一刻。
這是散文才問得出的問題。許多年前還未出書時,在一個聚集青年寫作者的座談會上被問及散文的虛構與真實,我好像回答過一個這樣的故事。那是關於某次在台大羅斯福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的地下道裡,遇見一個母親帶著三個孩子跪在地道裡乞討的事。她們的鋼碗旁邊豎立一塊紙板,寫有「丈夫跑路,女兒絕症,母子即將斷糧」一類的字樣。走過她們身旁時,同行的友人忽然說:「你相信嗎?你相信那上面寫的事嗎?這種到處都有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說。我無法回答。我真的不知道那紙板上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可是,一定有一種什麼『真的』東西,讓她們現在在那裡。」對我來說,那才是散文裡真正的真實。
十數年來,我經常在某些特定的時刻裡想起這件事。想起那時這樣回答的自己。還有在那個座談場合裡,說起這個故事的我。有時我會忍不住質疑,懷抱著這樣想法的自己是不是一種鄉愿或懦弱?十數年過去,有時我又會責備起自己,是不是已經忘了當時這樣想的自己了?這樣想的自己,當時究竟在想些什麼?
一一一年的年度散文獎得主是陳維鸚的〈等孩子長大〉。在《自由副刊》上讀到這篇文章以前,我並不認識作者,也從未讀過她的任何一篇作品。但這篇文章的開頭,在這個冬天裡,有時會忽然以一種聲音的方式,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接下來就交給我們。醫師戴上口罩前這麼說,然後那扇門就關起來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我當然沒有聽過作者的聲音。我想那是從我的心底山谷裡湧升的聲音。告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等待什麼呢?那是一種生活裡模模糊糊的感覺。像生活的陰影。我沒有文章裡那樣一個生病臥床的小孩,甚至我從來也不曾是一個母親。但那個聲音在我的心底響起時,很奇妙地,我彷彿通過了一條從遠方投遞過來的繩索,進入了他人的經驗。那時的我,既是他人,也是我自己。
這是散文離開「現在」的方法。儘管它離開它的「現在」就像只是從自己走到自己的影子這樣一步以內的距離。這樣的距離,像是離開自己去到自己的影子那裡,為了重新成為自己的影子回來看守自己。那些只有「自己」才能見證的「現在」。我們無比貴重的此時此刻。
謝謝這一年來所有錄記下許多此時此刻的創作者,以及寫作這篇文章的陳維鸚女士。所有此時此刻的必然,都來自當時越渡的種種偶然。理解這一點,我們或許能夠明白,我們正在經歷的、看似無有出路的當下,將是未來回望時的某種偶然。因此,在每一個看似被必然性所束縛的此時此刻,我們其實永遠都有選擇的自由,也永遠都有選擇不自由的自由。當有一天,未知的災難又把我們重新變成了嬰兒,也許這一年裡的某篇文字會使我們想起,還有人看守在時間中止的地方,等孩子長大。
而關於等待。這或許也是只有散文做得到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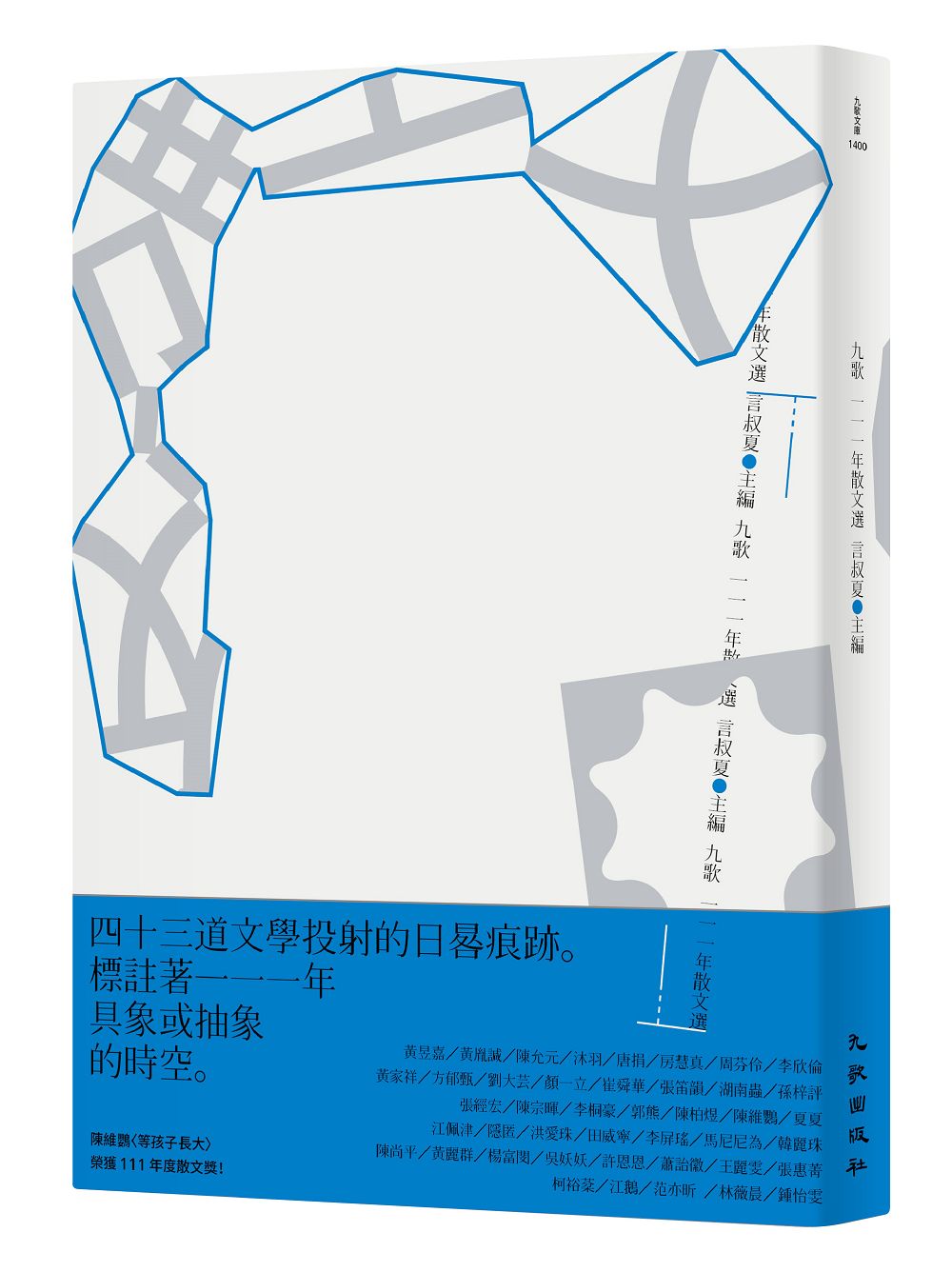
|主編:言叔夏
一九八二年一月生。有貓之人。白晝夢遊。夜間散步。
東華大學中文系、政治大學中文所畢業。現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曾獲花蓮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