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光臨夜台北人類觀測站——蔣亞妮《請登入遊戲》
我總習慣在片尾曲響起前離開一場電影,整理自己的衣物,把軟革鞋面上因經過一座城市街區而沾的髒汙擦去但始終擦不乾淨。我不回家,租賃在不夜城區的一個小套房中,付著和坪數不符的高額租金,只為從通宵營業的餐廳、居酒屋和便利商店裡二十四小時充斥的那些發光男女中,更靠近了解這座光之城。這城市與人們幾乎不睡,只偶爾寂靜,但寂靜也依然是不真實的,我曾經把水龍頭鎖緊家裡電源切掉,張耳在小小陽台上聽,雖然未曾確切的聽到但感覺得到,寂靜中有種哄然的、旋轉著的無聲,把那些如開機關機螢幕啪一聲熄滅的聲音全蓋過了。
我常常在轉角的百貨門口坐著,花整個下午到傍晚的時間張望著這條大街,隔著條小水溝,雖然水溝上橫亙的橋旁打上河名燙了金,但仍然是條大點的水溝,於是隔著這條水溝我看著兩端。水溝往西,是舊式大樓藏著小隔間的服飾店、美妝店,二輪影院和 MTV 也匿進其中。水溝東面,玻璃鏡面的大樓蓋著,鷹架圍住了城的天際線,這裡比起西城連路面都經常翻修,連鎖的影城圍住新大樓,但我通常留置閒晃的區域只在橋西旁三公尺的小貨車附近,在那裡買份鹹酥雞,加很多蒜跟九層塔,捧著它們逃出鷹架般的東城。更常在上班族都失神欲睡的午後,水溝旁看見某大明星從計程車上下來,用墨鏡和帽簷吸引更多的目光,可能穿著不合宜的配色或是剪裁失當的衣裙,走向橋東的途中未曾瞥我與身後背光西城一眼。更多的時候遇見那些不知名的少婦或是白日出沒的高䠷妙齡女子,在日光下仍發散著謎的夜晚香氣,不論年齡都一樣蒼白,她們不定轉向東或西,但她們臉上一定看不清情感與時間痕跡。
每到夜晚總得回家換上制服,我在巷口的便利商店打工,那裡有不停歇的冷氣和人群,有些在夜晚狂歡後感到飢餓、有些熟練的買著菸在店門吞下吐出,狀似等待,卻在菸燒近濾嘴時轉身就走,更多時候他們走進卻直接坐在店內的單人高椅上,喝杯咖啡買份雜誌,在人一變多時忽然離去,我看得太多卻從來不說,只用歡迎光臨與謝謝光臨遮掩自己觀察的視線。
那個阿嬤總在十一點多來,畫著浮出粉粒的妝和塗超出唇線的口紅,頭髮吹蓬,有著花露水和其他粉味在她周圍,那時她總已經提著許多東西,有透明塑膠袋裝著的乾麵,乾麵旁卻放著在路邊買的花朵髮圈,或是明顯不合她身材的緊身小可愛,她會走到冰櫃買一瓶啤酒和養樂多,每一次結帳時都會再重複次她養樂多是要買給孫女喝的,然後掏出張千元大鈔,我固定找她九百六十四元,阿嬤把零錢都放進她的塑膠袋中,但隔天總是再給我一張全新的千元鈔。我對阿嬤的印象極深,甚至深過那個每週末都會開著跑車載不同模特兒來買保險套的電影明星,店長才是真正見怪不怪的那個人,那天養樂多阿嬤剛結完帳,店長來店裡,店長卻說阿嬤從七、八年前就開始幫孫女買養樂多了,電影明星買的更久。
在深夜比較少人的時段,總要走到冰櫃後補飲料,穿上防寒的衣服,在低溫中卻異常溫暖,從不關上的亮白日光燈泡把店裡照成整條街上最閃亮潔白的一角,但卻得看太多這城市隱晦的陰暗面,叮咚的進門聲送進來一個又一個比電影精采並真實活著的角色,我從不抗拒的一一記下。兩個男孩在深夜進來,乾淨的臉孔和氣質,櫃台的同事專注的幫他們煮著咖啡,他們卻一閃身來到我藏身的冰櫃前,但對我不曾察覺,在狀似挑選其他飲料的手勢中,男孩們的另隻手在彼此身下摸索,從單薄的夏日短褲中尋找彼此,我無聲的補上其他飲料,不管男孩與男孩或男人與女人、不管是探索的手粗暴的手或偷走些什麼的手,這裡應有盡有,我在供應一切生活必需的商店中看到一切生活,然後歡迎他們。
凌晨,冬季時天色仍一片黑暗,分不清是霜或霧,總之氣味厚重,把停在門口的機車裹了一層露珠,換下制服後我買一杯奶茶微波加熱,一手拿著它另一手赤裸的抹去座墊上的水氣,因為這左右的冷熱感受,狠狠的打了陣哆嗦,然後坐上未乾的機車,以無聲滑過這座未醒的城,八線道的路面紅綠燈一路閃著橘黃燈號,當時速超過六十,這片黃燈便連成一片鎏金色系,在我到家之前天色便會開始亮起,鎏金融解露出了下面金屬骨幹的城市,一路接續到了我住的那片水泥斑落的牆,到達水溝橋面更西處,燦金過後只是灰。
金屬大門隔不住太多聲響,灰階石梯的五樓,走到時難免喘息不平。隔壁那戶人家是對母子,兒子慣例比我再晚些回家,他總在我洗完澡準備睡時大力拍著他們家的鐵門,短促而響,從不說話或按門鈴。每一次早晨他的返家就像報時,他重而忙亂的敲著但卻從不大喊,他的母親也未曾說過其他話語,只有巧遇時嘴角生疏而心虛的彎著一點弧度,在劇烈而粗暴的拍擊中我感到心安,悠緩睡去。
睡醒後我看一整天的電影,有時電影都看光了,就再去二輪影院重看一遍。平日時光中,極少去任何便利商店,因為那些自動快速的門後,可能藏著太多跟我一樣觀察的眼,我驚懼他們看向我,從我接住找零的手中紋路卜出我可能的一生,或從錢包內的物件猜疑來歷,城東、城西?或更南之境?
驚懼,只因為再熟悉不過那套便利商店占卜術,他們都是其他的我。
某夜,那女人在兩點四十走進,雨傘還滴著水就走了進來,像異時空的穿越者,她穿著一身時裝,黏著的兩層假睫毛半剝半落,眼影化成眼角的一片暈染黑洞,衣服簇新而她沾有陳舊的氣味。她在櫃架中行走,並沒有認真看什麼,只是神情一直往櫃台處漂移著,眼神中卻沒有我。我也常去天文博物館看那些星體的 3D 影片,只因我工作的地方太亮,星星比跨年的煙花還更難見。穹頂的星空中,彗星在宇宙內穿梭,微小行星的引力無法吸引她停留,商店裡,她在架上隨便拿了盒微波食品,在櫃台後我接住她透涼手下的物品,轉身按下加熱鍵,她的手扭著長鍊皮包的一端,扭得我跟著慌忙,黑色眼尾餘光在落地玻璃外掃著,一輛轎車停住按了兩聲喇叭,她扭的結更大了些,我無法卜出她的來源,她把手收在暖皮手套後面。
「再加熱一次。」聲音寒冷但眼神灼熱莫名,我不能再加熱,廉價材質的包裝可能會過燙融解,但還是按了次加熱的按鈕,嗶一聲之後開始旋轉,她接過零錢全都投進捐款箱,接過冒著過多熱氣的微波食品,她轉身走了出去長髮旋繞,像另一層迷霧星系,在可以清晰看出品牌的一身中,我嗅出了她一人竟擁有著整座城市甚至整個星系的味道,分不清方向。
「謝謝光臨。」
我聲音沙啞。
隔熱材質的黑膠擋住了車窗,她轉身看白亮過分的店門,眼神是一片空白卻折現出不知名光影。十幾分鐘之後我撈著關東煮裡的食材準備換新,才發覺光影只是眼淚,如此常見不應該忽略,看太多電影明星分不清藥水或哈欠的淚水,真實世界的眼淚發亮,明亮到不該屬於我們無法發光的身體。但我仍然知道,無法發光的我們只是因為遺忘,假如世界喪失了光源,那一天我們都會重新發光。
重新,因為我們的身軀還溫熱著,那一定是光盡後留下的餘溫。
過了四點半,週末,今天阿嬤與電影明星都缺曠了,我按開收銀台收起多的鈔票、打開用盡的發票捲上新的、下一班同事的機車排氣聲音極輕的在遠處響起,或許是他家樓下,一切清晰因城市靜極。我偷偷坐在店內高椅上喝微波奶茶,其實養樂多阿嬤的家就在我租屋不遠處,她在下午時澆花我在下午時早茶,整個百貨商圈後的地有一半是她擁有的,租給了茶街、租給了商城,一生未嫁。電影明星有恩愛的老婆,十年之前同十年之後,他永遠會在鏡頭前牽著老婆的手,那雙手也無數次一手接過找的零錢,一手捐出去發票。同事遲到了三分鐘,我回到櫃台,穿著一身夏裝的男人走進,身上被冬雨浸得半濕。
「歡迎光臨。」
他掏錢買了包長壽菸,轉身後我打卡,達達聲打在紙卡上,那一聲後城市的天開始亮了。
── 原文〈鎏金之城〉摘自蔣亞妮《請登入遊戲》

|蔣亞妮
畢業於東海中文、中興中文碩士班。曾獲南華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台北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等獎項。作品常刊登於中時人間副刊,並曾於《幼獅文藝》雜誌連載〈北京寫字〉專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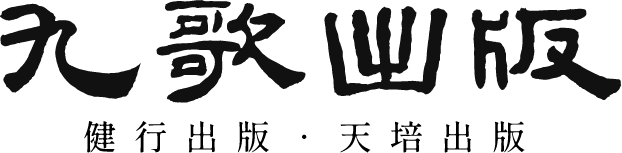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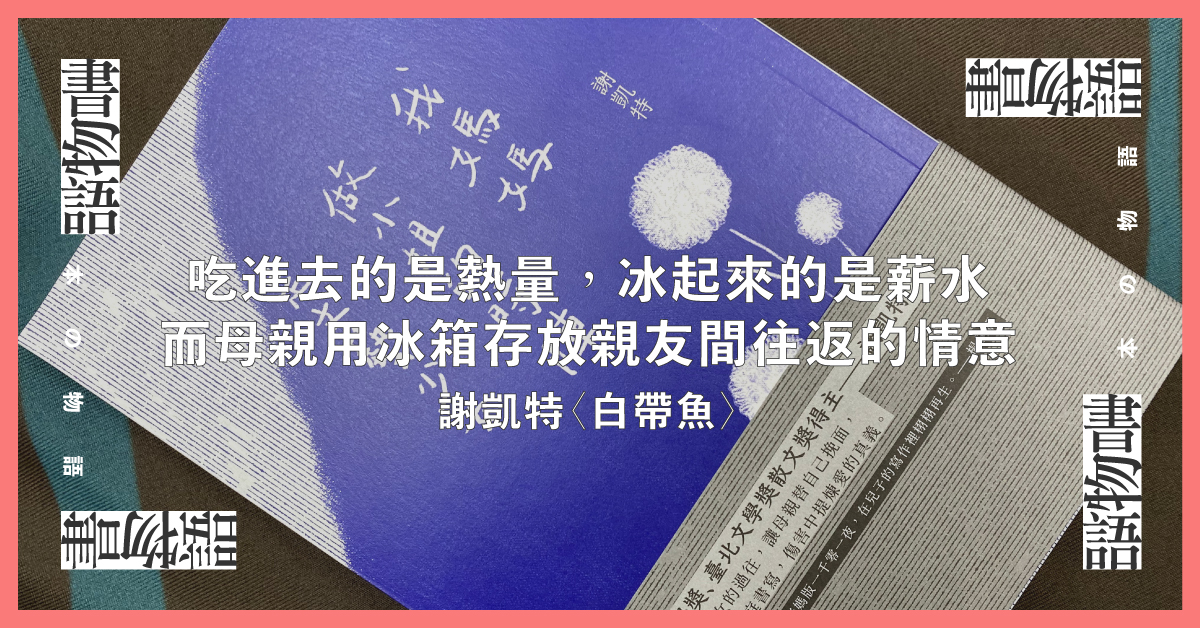

.png)